標籤:
.bwd.,
倉海君,
秘學鉤玄,
對話錄,
Zeke

(
Narcissus, by Michelangelo Caravaggio, ca. 1598.)
復活節期間,跟Zeke和.bwd.在Facebook討論Zeke最近修訂的文章《雷電,完美的意念 — 神的伴侶》,大家都想到了一些新東西,現在張貼出來,望大家不吝賜教。先錄Zeke的原文,再附Facebook討論於後。
雷電,完美的意念 — 神的伴侶
《頌詩 — 雷電,完美的意念 The Thunder, Perfect Mind , 在世行者譯》
我是自大能差遣而來,
我來到那些思慕我的人裡,
並展現予那些尋找我的人中。
仰望我吧,思慕我的你,
聆聽者的你,且聽我吧,
一直在守候我的你,
把我據為己有吧。
不要讓我離開你的視野,
也不要讓你所言所聞恨我,
無論何時何地不要昧沒我,時刻謹記!
不要昧沒我。
因著我是首先和末後。
我是被褒顯和被貶黜的一位。
我是娼妓和聖者。
我是妻子和童貞。
我是母親和女兒,
亦是母親的一部份。
我是不育的一位,
卻有著很多孩子。
我是那舉行盛大婚筵的,
然而我沒有任何丈夫。
我是從不曾懷孕的助產士,
亦是自身分娩之痛時的撫慰。
我是新娘和新郎,
亦是我丈夫誕下我的。
我是我父親的母親,
亦是我丈夫的姊妹,
祂亦是我的子裔。
我是為我鋪路者的役僕。
我是我子裔的管治者,
然而祂在我誕辰之先就誕下了我。
在預產期當刻,祂就是我的子裔,
我的能力是源自祂。
我是祂年青時的權杖,
祂是我年老時的拐杖。
一切如祂所願成就在我身上。
《在世行者言》
自埃及《拿戈瑪第古本》的神秘詩歌《雷電,完美的意念》。如此神性第一身斷言式宣告同樣可見於希伯來聖經《箴言》8 章:
我 ─ 智慧以靈明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
在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造化的起頭,
造化的起頭,
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
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
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祂立高天,我在那裡;
祂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
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祂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時,我在祂那裡為工師,
日日為祂所喜愛,常常在祂面前踴躍,
踴躍在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
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不可棄絕。
在這裡作自述的「我」 為陰性的「智慧」 (Chochma) ,根據上文《箴言》指她在神創造萬物之先已存在,是希伯來聖經中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外的另一造物者,以自己為世人母親賜予眾生生命,亦是膏立眾王的「生命樹」《箴 3:18》。被公教稱作「第二正典」的《德訓篇》(原為《本西拉的智慧》)之第二十四篇指「智慧」為「在一切創造之先的首生」,是「純愛、敬畏、智德和聖愛的母親」和「當受讚揚者」;《智慧篇》(原為《所羅門的智慧》)六至十篇則指「智慧」是「造萬物的技師」、「統治所造的萬物」並曾「拯救以色列人列祖」;古猶太以諾傳統中的《以諾一書》則記載「智慧」曾降臨大地遍尋不獲其可住處,繼而返回其原自處;《馬太福音》11:19 和《路加福音》 7:35 亦曾提及此女性神格「智慧 — 蘇菲亞」 (Sophia) :「智慧之眾子都以她為鑒」。從上述記載中可見「智慧」並非僅是擬人法而是實在和獨立女性位格,這就是古猶太的「智慧傳統」。
「智慧」與太初創世之「道」(Logos) 兩者一直有著相當的互換性,第一世紀猶太哲學家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 指「智慧」為一女性神格,同為神的母親、妻子和女兒,他把「智慧」與「道」為陰陽對等的二性 ,兩者共同分享著「神之首生」、「第一序」、「神的代理人」和「人神間的中保」的身份,此詮釋對日後猶太教及基督教有著深遠的影響;《約翰褔音》作者以斐羅對「道」的詮釋為基礎而寫成了序中的「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保羅在《歌林多前書》1:24 提出的基督作為「神的智慧」亦是受斐羅所影響;及後第四世紀亞力山大主教阿他那修 (Athanasius) 在抗衡亞流派時就曾提出「智慧」為神性之首生而說:「子就是父的『智慧』和『道』,且靠著祂並在祂之中創造萬物」;同代的尼西亞神學家維克多林 (Marius Victorinus) 亦相信「智慧」為三位一體的合稱,「智慧」和「道」皆是子的名字並強調「道」為陰陽二性;深受維克多林影響,奧古斯丁 (Augustine) 則指「智慧」為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在拉比猶太教及猶太秘學均把女性神格的「智慧」視為學習《托拉》(摩西五經)的終極奧義,且稱她為神的伴侶「舍姬娜」 (Shekhinah) ,意為「神的所在處」和「神的榮光」,她曾協助父創世、
作為雲彩降臨會幕及 代替父向眾先知顯現。自十九世紀起俄羅斯東正教中就有著一門專研神性女性位格智慧的「蘇菲亞學」 (Sophiology),為俄國現代宗教哲學之父索洛維耶夫 (Vladimir Soloviev) 受十六世紀著名的德國基督教神智學者伯麥 (Jakob Bohme) 啟發而創立。
在《拿戈瑪第古本》中被認為是《約翰褔音》續篇的《約翰秘傳之書》裡,基督在異象中向使徒約翰解說了天上地下一切的由來,當中提到在一切之上有一沒有名字的不可見之靈,祂超乎一般人認知所謂的「神」並凌駕於存在及時空等所有概念,圓滿自在於寂靜的永恆中,在猶太秘學中稱此在四字神名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之上的不可見之靈為「無量」 (Ein Sof) ,十二世紀自法國普羅旺斯的拉比阿伯拉罕.本.大衛就此曾解說:「基於祂比世上任何事物來得純樸,相比下祂就是『虛無』」。因著不可見之靈是圓滿自在和不假外求的,在祂裡面就不曾存在「我」這個概念,這樣祂便處於永恆的無我止境中。一息間,祂在光映中發現了自己的倒影,從而產生了祂首次的「自覺」,此「自覺」化成了一實在形體,那就是「智慧 — 蘇菲亞」,亦被稱作首意念「芭碧羅」 (Barbelo) ,《約翰秘傳之書》節錄如下:
祂獨自在圍繞著祂的光中睹看自己,
那是潤澤眾次元的活水之泉。
祂察見自己的倒影落在靈泉的各處,
便迷戀著這發亮之水,
基於祂的倒影就在這清澈的水光中。
祂的自覺成為了一實形,
在光芒中的一個她便應運而生。
她是先存於萬有的首道能力,是萬有的旨意。
她的光反映著父的光,是完美的能力,
是不可見童貞的靈之形像,
她是首道能力,是芭碧羅的榮光,
是眾次元中的完美榮光,是啟示的榮光。
她將榮耀頌讚歸于童貞的靈,因著她本自那靈而出。
她就是首意念,那靈的形像。
她成了萬有的母腹,本著她先存於一切。
她亦是父母一體、首人、聖靈、
三聯之子、三重能力、三名字、
陰陽並存者和在不可見的永恆次元中首現者。
「智慧」就是無我的不可見之靈的「自覺」,此一念將原來靈不可見的形像複製成了實形的宇宙首人「智慧」,為猶太秘學中神性從「無」 (Ein) 到「有」 (Yesh) 之序,亦包含著神屬性中不可知的超越性和無處不在的臨在性的相對關係。不可見之靈是寂靜不動的,祂從不會主動揭示自己及介入世事中,如此地上所有的救贖就是自其意念「智慧」而來,「智慧」不時降臨人間主動地揭示自己,作為反映著不可見的父之光的鏡子 (Ispaklaria) 讓世人能一睹神光,為斐羅強調「智慧」作為「人神間的中保」,這是為何《約翰褔音》 1:8 指「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智慧」作為反映父光的鏡子更能避免人們因直視神光無法承受而喪命的狀況 《出 33:20》(稱之為「神之吻」 (Meitah Be-Neshikah) ,阿伯拉罕、以撒、米利暗、阿倫、摩西皆是死於此情況下)。
一如猶太秘學所說,在太初創世、
降臨會幕和聖殿及向眾先知顯現的神性皆不是至高不可見之父而是其代理人女性神格「智慧」,首意念「智慧」就是在西乃山上以雷電展示神性形像者,為之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標題的原意。當摩西問及「神」的名字,所得的回答是「我就是我」(Ehyeh Asher Ehyeh,《和合本》作「我是自有永有」),如此神性第一身斷言式宣告就是「智慧」作為不可知的神之「自覺」向世人說話的特定模式,《猶太法典》 就曾提及摩西領受的「我就是我」之名為見神最清晰的鏡子,在猶太秘學中此名亦是所有希伯來神名中之首,對應首個流溢輪「榮冕輪」 (Keter) ,為與神性相遇最接近的距離。此「智慧」自述風格一直延續至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及《箴言》8 章中且重申著她就是太初的「第一我」,即太初與神同在的「道」《約 1:1》。此外,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遇見的「不滅火燄的荊棘叢」(生命樹)及
「雲彩」同樣為古猶太象徵女性神格「智慧」之物,他就在當中被「智慧」膏立從而轉化成一如天使般的神人,這是為何猶太釋經書《米大示》指摩西之銜 "Ish Elohim" 一字該解作「神的丈夫」而非僅是「神的人」。
在古猶太智慧傳統經常以「智慧」一如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中同時作為聖者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在猶太秘學經典《光明之書》(Sefer ha Bahir) 有著此描述:
祂將女兒許配給王者,視之為賞賜。
因著對女兒的愛,
有時候祂稱女兒為「妹妹」,
那是基於他們本是出自同一處的緣故;
有時候稱她為「女兒」,
因為她的確是其女兒;
有時候則稱她為「母親」。
「智慧」本自不可知一源而出,為之祂的女兒;「智慧」內在蘊涵著陰陽並存的神性,為之祂的妹妹;「智慧」在其內誕下了天上人子「細貌」 (Zeir Anpin) ,為之祂的母親。文中的「將女兒許配給王者」就是指神將「智慧」許配給所羅門王《王上 5:12》,成了所羅門王的妻子;所羅門王和「智慧」同自至高者而出,就是所羅門王的妹妹;所羅門王本自「智慧」膏立而得真生命,就是他的母親。
在《拿戈瑪第古本》另一名為《宇宙之源》的經典指「智慧 — 蘇菲亞」自不可見之靈流溢所生後創造天地萬有,她將其自身內在的女兒「祖貽」(Zoe,意為「生命」)許配予
天上人子撒寶特 (Sabaoth) ,在創世時將氣息賦予阿當使之成為活人,並差遣
祖貽到人間成了眾生之母夏娃以協輔阿當。這樣,她既是天上神性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亦是地上阿當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在《宇宙之源》中有一段與《雷電,完美的意念》極為相近的蘇菲亞祖貽自述:
我是我母親的一部份,亦是那母親。
我是妻子,亦是童貞。
我是有身孕的,亦是助產士。
我是撫慰分娩之痛的那位。
我是自我丈夫誕下的,
亦是他的母親。
他既是我的父親又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力量,
一切他所欲的,他必帶著理由說出來。
我是成就的進程,我亦已生出作為主的人。
此外,耶穌身邊不同的「瑪利亞」亦可見「智慧」同作母親、妹妹和妻子之說,自《拿戈瑪第古本》之《腓力福音》的段落:
三位常與耶穌為伴的瑪利亞,
就是祂的母親、祂的姊妹、
和那位被稱為祂的伴侶抹大拉。
祂的姊妹、祂的母親和祂的伴侶為三位瑪利亞。
「阿卡莫特」(Echamoth) 和「阿克莫特」 (Echmoth) 為不同的兩回事。
「阿卡莫特」簡而言之就是智慧,
「阿克莫特」則是死亡的智慧,
那認識死亡的一位,
且被稱為「小蘇菲亞」。
耶穌母親瑪利亞乃是「阿卡莫特」(意為「智慧」)一直養育肉身的耶穌,為
天上地下沒有任何力量能污損的童貞, 稱作「大蘇菲亞」,如此對照可見於俄羅斯東正教之蘇菲亞學中;而耶穌的伴侶抹大拉瑪利亞則是「阿克莫特」(意為「有如死亡」),她在十架下及空墳之前作為執行耶穌之體被釘死的贖罪祭之女祭司,稱作「小蘇菲亞」。她們皆得著從上而來的智慧,一如摩西姊姊米利暗(Miriam,希伯來文的「瑪利亞」)作為協輔救贖者,籍著她們使道成肉身之計劃得以成就。
按《雷電,完美的意念》所述,「智慧」既是母親、女兒、妹妹、妻子、新娘和新郎,更是童貞 和聖者,這裡的娼妓不是貶稱,其希伯來文 Kedesha 與「神聖」 (Kodash) 為相同字根,而「娼妓」、「聖靈」 (Ruach ha Kodesh) 、「童貞」和「智慧」此四字乃是古代近東對女性神格交替使用的尊稱,這是為何抹大拉瑪利亞同樣被指為「娼妓」。
如此我們就能解讀《多馬福音》105 教人不安的論述:
但凡認識父和母的,他必被稱作娼妓之子。
但凡認識永生之父和智慧之母合一奧義的,就能一如摩西、所羅門和眾聖者般得著女性神格「智慧」膏立而得著真生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討論.bwd.:I think the status of 圓滿 denotes a 究竟的(修行)境界? I have a little book about Buddha’s life here and it states 佛有三身: 法身, 報身, 化身. 法身 is like The Unknown One: “法界之性, 離一切自性, 無一實體可得, 所以佛的法身雖遍滿虛空法界, 卻無大小之分, 亦無多少、有無、來去、生滅等一切計度分別。” 化身則為世人可見之體, 例釋迦牟尼佛, 世人可觀其修行及經歷生老病死以世事無常之理, "亦能以化身之力從虛空中及樹木草石等懸崖等無心之物, 發出法音演說諸法真實義", which is like Barbelo, a visible side / emanation / part of The Unknown One, who is himself invisible and indeterminate, and Barbelo is the “part” to do the awakening work (because she is the visible side), while The Unknown One remains in Silence and 虛空. Buddha is with the status of 圓滿三身, which can then be best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eople.
Zeke:I've asked Tom yesterday and got the term 無明,無始無明 is similar to the Invisible One, while 一念無明 is like The First Thought Barbelo.
Quoted from 《楞嚴經》: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必明即是無明,無明乃為結妄根本。
倉海君:1.「必明即是無明」?似乎不是這樣,請參考以下網頁:http://www.fosss.org/jcxs/sjcy.htm
Barbelo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细」之「動相」。
2. 「祂察見自己的倒影落在靈泉的各處,
祂便迷戀著這發亮之水」
迷戀二字很有意思。我認為此「迷戀」其實就是創世首日之光:Zohar以此光等同sefirah of Hesed,而古羅馬詩人Lucretius在其《物理論》(De Rerum Natura)卷一也稱愛神Venus為萬物之母。奧維德(Ovidius)的《變形記》(Metamorphoseon Libri)卷三載Narcissus故事,我懷疑原型可能是一段與Barbelo相關的創世神話--這是很離經叛道的解法。一般人只留意到這故事以「自戀」為主題,卻忽略了很多細節,例如Narcissus出生時,失明先知Tiresias已預言「除非他將來不認識自己」(si se non noverit),否則不會長壽。何謂「認識自己」呢?原來Narcissus愛上水中倒影之時(二元分裂,即「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後來當他覺悟到「他就是我」(iste ego sum),卻苦無方法合一,便悲慟至死,形影俱亡。他的影乃由愛慕所生,因為只要他「一轉身,所愛者便會消失」(quod amas, avertere, perdes),然而他卻終日凝視自己,幻象便恆住不滅了。不要忘記Aristotle的神,就是「思想自身的思想」(he noesis noeseos noesis),相信也是Plato甚至更遠古的哲學家遺教,所以我推測Narcissus根本就是由這個至上沉思者發展出來的象徵。另外,Narcissus有一個他不欲接受的「伴侶」,叫Echo:她本來有肉身,後來只剩下聲音。如果美少年倒影是「第一念」,那麼Echo便順理成章扮演《首念之三形》中「聲音」的角色了。
一個有趣的問題:Narcissus未見倒影時,當然沒有「自我認識」,但見到倒影而迷戀它時,又是否有「自我認識」呢?抑或他只是「自我誤解」?我個人認為是「誤解」居多,儘管其「認知」程度可能較最初的「無知」為優。然而自我認知會否陷入困局,即把自我分裂為二呢?天地萬物的創造,又是否源於神的一念無明及祂對自我的誤解呢?(我傾向相信是)
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當然,相對於神是幻象的,對我們這些幻影而言就是真實了。
3. 最近我在讀古羅馬作者的詩文,發現很多有關Sophia的論述,很有趣,稍後有空再撰文分享吧。另外,我對Fideli D'Amore很感興趣,不知大家曾否對此神秘團體略有所聞?
Zeke:謝謝,當中點出好幾個極具啟發性的關聯。就創世原型問題,對照 NHC 中 Sethian 及 Barbelognostic 幾個流溢創世版本,從不同版本中細節上的差異可見它們不可能出自同一材料或曾互相參考(除了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和 The Hypostasis of the Archons),然而,它們卻像是從不同的口傳而來,這些口傳卻同時指向著相當同一原型。一如你提出的,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Kabbalah 生命樹亦是如此,其對應的五相就是委婉地表達著米索不達美亞的多神神譜和他們古希臘哲學式流溢關係。
NHC 中的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一如你提出把 Venus (Aphrodite) 等同萬物之母:
The second Adam is soul-endowed and appeared on the sixth day, which is called Aphrodite. "
我不認為是這樣的神話角色挪用是大雜燴,我反而認為這樣的挪用表示了當時社會就不同神話間的人物互換有著相當的共識,一如 Magical Papyri 那樣。
Fideli D'Amore 我只知道他們沿用著回教秘學的整套系統和術語,大概是派別的創始人曾受回教秘學的啟蒙,在中世紀初有好幾為西方及猶太哲學家均受當時的回教秘學影響。
.bwd.: 噢, 搬到這邊來哪, 那我在這兒再請教數個問題:
"見到倒影而迷戀它時,又是否有「自我認識」呢? / 我個人認為是「誤解」居多 / 天地萬物的創造,又是否源於神的一念無明及祂對自我的誤解呢?(我傾向相信是)" - 請問你所指的"誤解"是指誤解了甚麼呢?
我覺得天地萬物的創造, 源於至高者的一念, 但在整個創造的舞台上, 也就只那一念, 然後, 祂復又回歸到那深淵。也許是因為祂是完全超脫的, 不可名的, 所以經典上談到祂時也沒有多談祂在創世(指這個世界)的角色只集中談祂的不可名之性。"約翰密傳"開篇便花很多篇幅談到祂的不可見、無以量度, 祂不屬於完美或受祝福或神聖, 因為祂根本超脫這一切。而這些經典用到的字眼, 大多是"存在", 比方說, 在"Allogenes"裡, 對至高者的描述是"He exists as an Invisible One who is incomprehensible to them all. He contains them all within himself, for they all exist because of him. He is perfect, and he is greater than perfect, and he is blessed. He is always One and he exists in them all, being ineffable, unnameable...", 可不可以這樣說, "存在"本身是可以沒有"意識到自己存在"的, 就是說, "存在"本身是一個自在的境界, 是沒有任何主體或客體的認知的。同一經典寫道"it is he who shall come to be when he recognizes himself", 語氣上好像沒有談到祂有"創造"的"意識", 只有"自我"的一念。就是說, 祂的一念, 原不為創世而生, 但祂的一念又確實是流溢的源頭, 因為祂的一念(並非有意識或有目的地)流溢了第一念, 之後有其他的流溢, 而我們世人就是通過第一念(可被認識的)才能認識至高者(不可被認識的)。
"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 - 請問你所指的"自己"是誰? 是至高者嗎? 還是我們凡人? 如果是後者, 我倒相信這光是無時無刻拂照著我, 不過我駑鈍, 還未"看到/感到"。
" 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 - 請問, 遠古的近東是不是文明的源頭? 是不是各種宗教都始於它們? 我在歷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可說是連common sense也沒有, 最近讀一些有關Freemasonry的書, 都由埃及談起, 中間又談到很多神話, 真的讀到頭大。
不過, Freemasonry和Kabbalah的關聯還真有趣。有位叫Guérillot的學者將Scottish Rite中10個Degrees和生命樹各輪做了對照, 出奇地吻合呢。
又, Narcissus見到自己的倒影時, 他意識到那個倒影是他自己呢, 還是認為那是一個他者? 他迷戀著自己的倒影時, 是迷戀著"自己"/"自己的美"呢, 還是迷戀著一個自身以外的"他者"?
自己(一) -- 鏡子 -- 分裂(多於一) -- 意識?/沒有意識? -- ?? -- 合一(一): 這個概念很有趣。
倉海君: 我的想法很簡單:至高者一念成象,頓生依戀(即「光」),由是象復生象,前後相逐,往而不反,既遺忘了自己,亦幻生出宇宙萬物。這過程很簡單,你每分每秒都有此經驗(特別是「遺忘自己」),思想本身就是創造/流溢--不論你有意還是無意。我們一直都在感受着類似創世的過程,只是我們不察覺而已。
我所謂「誤解」,指「不知道那一念而生之象就是自己的思想本身」;正如在水仙花神話中,Narcissus本來也不知道倒影就是自己(有人認為這版本太無稽,便插入孿生姊妹一角,說Narcissus臨泉自照,是懷念已死的姊妹)。換句話說,在創世之初,至高者根本沒有自我意識或知識,而只是一味追逐那作為他者而存在的念頭,且妄執為實,是為「誤解」。至高者的幻想,相對於我們就是現實,所以當祂真正「認識自己」--如Narcissus頓悟倒影之因由--並把其意識流斬斷,萬有就不復存在了。
如Tiresias所預言,Narcissus「認識自己」後便死掉,這裡牽涉一個詮釋問題:死亡是否意味一種解脫呢?Ovid詩中記錄了Narcissus一句話:「死亡於我亦等閒事,因為我可藉死亡而放下煩惱。」(nec mihi mors gravis est posituro morte dolores)不在人世,焉知不是美滿結局?萬有皆寂,宇宙反虛,又有何不妥?說到底,生和死都是同樣令人驚嘆的奇蹟。
最後澄清一點:"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 --「自己」即至上神自己。因為祂一直都不能完全認識自己,所以--照我上述的理論來說--世界萬物才可能像現在般存在。
Zeke: 在自戀情意結中的人們往往把「自我」和「他者」混淆在一起,就像追逐鏡子裡面另一塊鏡子的形像,在追逐過程往往讓人忘記最原來的本像,這樣下層的智慧方會作出單方面衍生 Yaldabaoth 如此無知之舉,繼而 Yaldabaoth 自以為「『我』就是神,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神」,宣告「別無他神」那就代表宣告者必須以否定他者才能肯定自己,是缺乏自我認知的表現,不同程度地重覆著不可見之靈自戀衍生首意念的模式。只有不自足者方會無止地追求財富和權力,只有不完全者才會強迫別人相信他是獨一真神。
一個人每天打扮為求愛侶的讚賞,這樣他的愛侶就作為了他的鏡子,讓他從中模造一個能讓別人愛慕的自己,一切源於他的本我對被愛的執著,然而此舉卻無法成就肯定本我的原意,基於靠著打扮而被愛的過程是無止的,是徒勞和無法自在的。
在《約翰秘傳之書》和 Allogenes 中分享著的否定句式段落指出不可見之靈的屬性並不在於祂是什麼,而是祂不是什麼,以彰顯其最原來「無我」的不可知性,稱為 Apophatic Theology 。一如妳提出的,「存在本身是一個自在的境界,是沒有任何主體或客體的認知的」,既是這樣,真正的存在是無須以任何理性及外在因素去證明,亦只有從這些因素中抽離方能達至那自在解脫之境。
就「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在我現時能定案範圍那是米索不達美亞的神譜結構及神話故事內容對日後的希伯來聖經及猶太教之影響,當然其可涵括範圍應為更廣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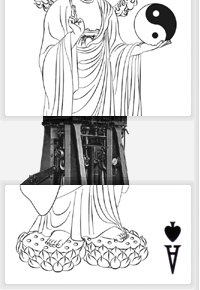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造化的起頭,
造化的起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