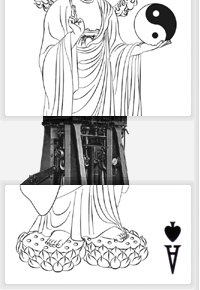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母:(見門縫透光,拍門)仔,你又咁夜都唔瞓覺?十二點喇,快啲去瞓。
子:唔得呀,我未溫晒書,十二點半先啦。
母:好啦。
半小時後
子:媽,可唔可以幫我校鬧鐘聽朝四點起身呀?
母:咁早起身做乜?
子:溫書囉,放學之後又要上英文班,又要學小提琴,都無時間畀我溫書。
母:好啦好啦,早抖喇。
半年後
子:媽,我入到華仁喇!
母:叻仔,入到英中你以後條路就易行好多喇。
五年後
醫生:由於佢發育時期長時間睡眠不足,影響腦部發展,以致智商下降,林太我建議你唔好畀咁大壓力佢,等佢休學一年,下年先再考會考喇。
子:我要考會考…我要考會考…
4時起脇溫習 苦讀生圓英中夢 叩門激烈 一英中56人爭1學額 (明報) 07月 09日 星期三 05:10AM
童年
斷正
小息。
「陳芷玲,maths,快!」
「Prefect 喺度呀仆街!」
「走咗喇,快啦,一陣就 maths 堂!」
「嗱。」
「喂你做緊乜?」
「sor 呀張 sir,尋晚唔記得做,而家仲做緊。」
「你當我盲?收埋本簿我就睇唔到喇咩?攞出嚟啦。」
「陳芷玲你做乜借佢抄?」
「無呀,我擺喺枱面諗住一陣交,小息完咗返嚟已經揾唔到。」
「係呀,係我自己攞咋。」
「今個月第三次,呢個學期第七次喇喎黃同學,我好難唔記你缺點。」
「哦。」
Lunch。
「做咩吸煙?」
「讀書壓力大囉,A level 辛苦嘛張 sir。」
「咁大個人都唔知吸煙唔啱?」
「喂我過咗十八歲喇喎,法律上我可以食煙,你憑咩講啱唔啱先?」
「仲唔認錯?吸煙已經記一個小過,唔認可以記多你一個。」
「校規唔俾我食,而家斷正,我又無唔服又無唔認。你一年捉幾百單抄功課,個個都話自己攞人哋份功課,九成九講大話啦,又唔見你記多佢哋一個缺點。」
「好聲好氣同你講,你仲要咁講嘢?」
「阿 sir 你冷靜啲,我一早認咗,唔信你問捉我個 prefect。」
「見你第一次,而家記你一個小過。」
「哦。」
「咪話陳 sir 唔幫你,唔係就記你兩個小過。」
「多謝阿 sir,其實一個定兩個都無咩分別。」
「咁我叫張 sir 改返囉。」
「唔使喇,唔好勞煩佢啦。」
「總之以後食還食,唔好喺學校食啦。大個喇你,顧吓自己身體啦,唔好食太多。」
「知道喇。」
放學。
「詠佩,你知發生咩事啦?篇嘢係咪你寫?」
「係。」
「你知唔知而家搞到好大件事,我哋幾個老師、副校長為咗你要開幾耐會?」
「對唔住呀 miss,我真係無諗過會咁,嗰陣我已經即刻講咗對唔住喇。」
「唔好講咁多喇,而家記你一個大過,當係個教訓啦。」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延伸閱讀:
網誌幸災樂禍 女生被記大過
來函鄺恩瀚:從記大過看社會價值觀
附筆:指責「網民」「愈來愈容不下非主流的聲音」,其實我們的社會、教育制度何曾容得下?反而在網絡上才讓非主流的聲音有機會發表,問題的根柢在於我們的 社會風氣、學習環境如何對待其他意見不同的人。而且,視「網民」為一個整體,只着眼於起底組的工作而忽略反對起底的聲音,然後視網民為暴民、民粹主 義,這類針對網絡生態的評論已經太多了,多得近乎陳腔濫調。
語文教育私議 (作者:Y.T.)
嘗與衿契論語文教育。竊以文者字為本,習文豈有不以學字為先?許慎說文之旨,一在細疏字義。字義既明,造句屬辭,自可穩健,毋令學者但憑上文下理,而胡揣其字云。
聞近年香港語文教育,唯重理解而輕背誦,此其大謬者也。試觀乎古德明,陶傑,董橋,金庸,岑逸飛,司徒華之輩,未有輕夫舊學根基而能文者也。自古為學,皆云苦學,去其苦而欲其成,不如悉絕其學,了其餘哀耳。
或曰:上者姑可如此,下者不能也。
曰:非也。古之生童,悉從課字誦書入手。不成一代鴻儒,猶可點竄塗改,達意文章,畢生受用。豈昔者知而今者愚乎?今之人其不忍太過耳。以為童子無憂,洋洋而學,則必奮思自通,創意如泉矣,殊不知其有思而無學,欲言而亂語,如此之弊,萌夫一代而禍夫百年者也。
今之世也,求學如購物,何哉?媚客之風(consumerism)熾也。於是文教不興,必罪師長制度,所謂革故鼎新者,悉以曲護生童為務,苦者裒其苦,娛者益其娛,則禮曹相慶,眾口囂囂,以為必成其教矣。嗚呼。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昔者,窮村陋巷猶有讀書之人。布衣而至卿相者,奕代有之。足見古之學者,不盡世家,苦學之道,無違普教。然則學而未之達者,如之何而可也?曰:下者,即令其學,不學,可以罰,復不學,可以退之。
古之治人者勸學,故學者皆自勉;今之治人者逗學,而學者泰半墬其志矣。夫訓令不行無以治兵;威嚴不立無以勸學。賴夫營謀之心而勸,消費之心而學,而能有功於文教者,吾未之聞也。
或曰:學,弗止於文。當今之世,德之衰,有甚於文者也。
曰:夫學問萬殊,文固止其一耳。中下者不能,可使之試覓他學,或就其才亦未可知。然則,苦學之理,非以棄之也,望其惜學而益奮發耳。苟有屢試而不能者,憫之也,助之也,非以浮言而欺之也。近歲尺度日寬而學子日惰,甚有自欺而日驕者,其不可悲乎?
至若德教之不足,余固深痛之也!惟童稚無知,或可授之淺理,其至者則不可。及其長也,方命明辨慎思之功,同年講習,抵論切磋,是循其知而成其德之道也。夫君子之學也貴慎始。童稚之時,一言一行,皆有深致夫其潛意識 (subconsciousness)者,而理之所及,顯意識(consciousness)而已。範之以規矩,而後授之以道理,此慎其始而明其終者也。文亦如斯而已。
香港學生的理解能力
聲明:當然,只是「部份」學生(不作聲明的話,總有白痴會跳出來指我「以偏概全」)
on.cc--考評局荒謬機制
HKEAA--考評局怎樣處理覆核成績申請
「首先,一些考生明明得到了c級的成績,但因為考評局的疏忽下只能取得d級成績,而覆核成績後又要得到比一般c級成績高才能得到c級,這對那些考生極為不公平。」
考評局的網頁則這樣寫:
「以上提升準則不適用於涉及錯誤處理分數的答卷。在此情況下,即使是一分之差,只要答卷的新積分達至上一個等級的最低分數,成績仍會獲提升。」
律師為何見錢開眼?
剛讀過下面一篇叫《我和我的高考》的文章,覺得極有趣,那時候預備應考,整天埋首什麼斷代史,Concert of Europe,Eastern Question,把光陰虛耗在這些沒大用處的東西上,現在回首實覺得是種罪孽。這些東西學罷又如何?在現實生活無所用,跟百多年前的八股文一樣,考生的時間是花了,記了滿腦子人物時間原因影響,但在工作上沒半點用途,天下間很難再找到比這樣更大的罪孽。
撫心自忖,我唸了廿多年書,考過無數試,最可怕最凶險的那場考試就是律師執業試,差點兒要了我的命,高考跟它相比,簡直就如叫街上一個還沒發育完整的女孩跟Bay Watch的女主角Pamela Anderson比胸圍尺碼,小巫見大巫。高考頂多只有五六科,但PCLL(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有八科:Conveyancing, Wills and Probate, Civil Procedure, Criminal Procedure, Advocacy, Commercial Law and Practice, Professional Conduct及 Solicitor Accounts,其中猶以Conveyancing, Civil Procedure,Commercial Law and Practice最駭人,單是一本書都有幾吋厚,倘若加上那叠即使不眠不休也看不完的案例,現在想起仍猶有餘悸。教師對學生沒絲毫體諒,擺出一副刻薄臭咀臉,好像跟你說「讀唔讀呀契弟,唔讀咪唔好practise囉。」同學之間又爾虞我詐,最愛把有用的參考書藏起來,跟你玩尋寶遊戲,儘管你使出了吃奶的力尋遍整間圖書館,也找不到個書皮,掛在眾人面上的彷彿就是一句「唔係你死就係我亡」的訊息。跟他們坐在禮堂考試的感覺跟與老虎豺狼在撕殺無異。同學間除了少數人外,根本就不會守望相助,在學習上互相切磋,巴不得你考試不及格拿不到執業資格,少了個競爭對手。你若有問題要向同學請教,他們就愛裝蒜對你說不清楚或敷衍一番。律師就是在這種環境裏調教出來的,所以律師的陰險卑鄙和心計是幼承庭訓,只有愚不可及的市民才相信律師會捍衛正義,對不起,捍衛正義是幻想世界裏超人、蜘蛛俠、神奇女俠才幹的,現實世界是沒有人去捍衛正義,聽起來頗殘酷,但除了接受外,你又能怎樣? 我並非指沒有具正義感的同行,但他們的數目跟中年漢的煩惱絲一樣,愈來愈少。
眾所周知,律師另一職業病就是「唯利是圖,視錢如命」(跟那些經紀沒兩樣),但又有誰知道這種心態是被迫出來的。普通學科的教科書頂多二百多元一本,一個學期買兩至三本,已經足夠有餘,因為不少大學生手裏拿着那十多廿頁的講義,已足夠應付考試,但讀法律則不然,一本教科書隨時要五百至六百多元,有時為了省時,要買多部案例書,如此算來,花上九百多元去買一科的教科書不足為奇。你也許會問,為何不去圖書館借閱? 倘若整本五六百頁的教科書都是考試範圍,沒有一頁不用讀,莫非你能按耐得住小腿的酸痛站在圖書館的影印機旁大半天去影印麼? 有位教授法學理論的老師解釋說﹕「因為出版社認為你們將來畢業後能賺回這些錢,所以把課本零售價調高點。」真想不到塵世間會有此悖論歪理。試想想在四至五年的大學生活裏,法律學生被人搾出了多少血汗錢? 從前看粵語長片初歸媳婦必被譚蘭卿飾演的奶奶痛罵虐待,及至這位媳婦做了別人的奶奶,她又以此道施於她自家的媳婦上,同樣道理,少年時被出版商敲詐,畢業後便去搾取別人,委實無可厚非。
大細

話說某個地方有一個賭場,政府規定所有年輕人如要飛黃騰達,得先進去賭一把,於是當地不少青年均把青春押注在鑽研賭術之中。如是者,幾代以後,當地居民也會叫自己的兒女努力學賭。
賭場中的其中一位曉得各種賭術的荷官姓高,所有希望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輕人最終必須挑戰他。
挑戰的方法是,跟他賭四至五種不同類型的遊戲,其中必須要有大細以及輪盤,全勝者方算成功。
他每年只會跟年輕人賭一個月,往往是贏者少輸家多。
有一次在賭大細時,高先生連開十幾次大,賭場決定換骰。
再開,又一次大。
於是,翌年再賭大細時,不少人均押注買「大」。
結果,開細。
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新聞。
另附送補習名師 Jeffrey Hui 所撰之聯署反對聲明。
我和我的高考
會考與高考都在進行,在此轉貼Lestsariel幾年前舊作一篇,以餐享在會考及高考的讀者
作者:Lestsariel
無疑,高考是屬於我的><
如果說,開學前,那個腳蹬學生皮鞋,肩揹單肩式大書包,身穿新學校的白色校服,整日奔波在那堆苦了學生的書本中的十七歲年輕人,還沒有意識到,命運已經把一個可悲可憐的考試交給了他,那麼,今天,當我真的面對高考,並第一次挑戰它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和我的高考已經無法逃避了。
不久之前,我和朋友們在某家大學看見了一本《高考學生們的備忘》。出於甚麼呢?我立刻把它取下書架,幾乎是下意識地,隨手翻到了那一頁。
是的,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三年高級程度會考第一份卷開考
我又看到了我的高考。我的災難深重的高考。我的傷痕纍纍的高考。我的那大毀滅的九死無生的高考。高考,它理所當然要和世界歷史,人類發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類所銘記。
高考生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忌日。這些日子,每當想到三月二十八日到來的時候,考生的房就有一些書本在晃動著。悄寂無聲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紅的火苗。火光裏映出的是一雙雙愴然的眼圈—文科生的,理科生的;也映出了他們手中一張張死背著的notes—
文學—進學解
中化—人生的意義
中史班超的貢獻
晨曦中,一整夜的水氣化作的煙,由絮絮縷縷漸漸融合成一片,是白色的霧,浮動在新建的高層試場間。煙霧在空氣中飄浮著,它們是孩子眼中一片片神奇的下降白雲,降得很低,又不能觸摸。飄到路旁的草叢中,飄到飲過雞精的考生的密麻notes上。他們沒有理會它,他們的眼晴在癡癡地望著notes,不,是在背notes中的那個世界,考生的嘴唇顫動著,在喃喃的訴說著甚麼。
我曾不止一次走過那些死背的考生的房間。我理解,在高考,「三.二八」考試的死難者們是沒有墳場的;那些有低分的各張Paper,那些有U的試卷,那些在覆檢後重新評F的考卷,甚至即將派發的成績表,都是他們無碑的墓地。考試前,他們就是為這些考卷,被睡魔折磨,被灌下奶茶,被書堆和Notes活活窒息的。考試後,notes已不復存在。然而我認為出一切。我走著,從路邊丟著書本厚的文學的歷史的notes,走向雜亂堆起的中史的書本。是一個無月的夜晚,我獨自乾啃著一堆高考時要用上的notes,忽然發現,咖啡旁那一本本高大的西史書,通本英文,閃著奇異的光。這些在高考中,要像櫃中漫畫一樣頻密翻動的厚書,這些曾目睹過高考一幕幕慘狀的書本,它們考完還在默默地、忠實地守護著甚麼呢?那一頁頁形狀彎曲的英文,使人想到它清楚的記載。兩年來,書本的字體一點一點地記在高考生死背著的腦袋深處,是在為A grade和E grade,大學和失業選擇著甚麼前程呢﹗
高考,是迄今為止四百多年世界考試史上最悲慘的一頁。香港考試局出版的年報一堆,向全人類公佈了這一慘絕人寰的事實︰
U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九份
F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份
每當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我的心便會一陣陣發緊。
上一年中六畢業試的試題是極為可怖的,貼錯題引起的次生災害—錯答幾乎覆沒了全份試卷,U左計十萬份。
今年二月中七畢業預試,引起了橫掃全中七的錯答,題目直殺考生,將大交叉畫上考生的試卷。這次考試的U卷,總數近七千份。
還有今年三月小測,冷題,僻題,難題,怪題,總共使一百七十八份卷U。
這些數字意味著甚麼?它們意味著︰高考的U卷數,是舉班震驚的中六畢業試的二點四倍,中七預試的三十五倍,三月小測的一千三百多倍﹗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數字背後人的悲慘命運。政府盡可以用數十億美元,數百億美元來救濟失業的考生,可是又能用甚麼來計算升學機會的損失呢?失去的機會是無價的。
太難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難了。
不久前我訪問過一位考生,在她家,她給我端出咖啡和糖,出於禮貌,我請她也喝。她卻連連搖手︰「不,不﹗」她說,「高考之後,我就沒喝過一點咖啡……」,她告訴我,她是在書堆中溫了整整一月之後才考過來的,考試時喝的唯一飲料,是滿滿一壺咖啡。從此,一切咖啡有關的東西都會使她產生強烈的厭惡感。咖啡糖、咖啡巧克力、甚至鴛鴦……這一切都會使她喚起高考時在書堆裏讀得幾乎要發瘋的感覺。「我不能喝咖啡,我受不了」,高考後,苦澀的滋味一直沒有離開過她,一直沒有……
「經過高考的人,都像害過了一場病。」另一位考生對我說。「我一到書架,一到自修室,人就說不出的難受。腦子堵得慌,讀不進書來,只想睡,只想伏在桌上……」她不止一次這樣睡在自修室內,哪怕管理員吵醒了她,趕她離開,任他們怎樣鬧也鬧不醒她。她會睡﹗她是壓在書堆中睡了三天後才溫書的,她至今還牢牢地記著那催眠了她三天的悶蛋的書堆是甚麼樣子。平時只要字體變細,當時那昏昏欲睡的感覺又會回來,令她睏睡。考完了,是甚麼無形的東西還在殘忍地催眠著這無奈的考生呢?
你,一位中年考生,語調十分平靜,平靜之中又透著說不盡的酸楚,「那些傷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嗎?當年,為了救起你的文學,你曾在notes堆中扒了整整一周,是一張沙紙最終將你的希望斷送。你告訴我,文學是單單肥了在那張讀本中的,你當場哭了出來。怎能夠忘記啊﹗那是一張可怕的卷。採訪中,曾有人揚著沙紙,指著表上的F對我說,偏激肥了中文的口試,這是考官的偏見烙下的……
還有你,老考生羊祜,我在你冷清清的家裏坐著,看著你竭力作出輕鬆的笑,我真想哭。「考試前的那天晚上,我溫過了鄭和。夜裏十點鐘還跟同學通了電話,是女朋友聽的,她問︰『喂喂,我要溫張騫你陪我溫沒?』,我說︰『不好啦。』她又問︰『為甚麼不?』我說︰『今年不出的﹗』她問我肯定不肯定,還要我一定陪她溫……」你說不下去,老淚順著滿臉的皺紋往下渦。考完了,你至今還藏著那份出了鄭和不出張騫的中史卷,像是珍藏著和女朋友一同入大學的心……
二十四萬個U彷彿就是這樣一份一份累積的。
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肥了的二五五試場,是我這次去考試的主場。試場有一塊小白板,保存著部份肥了的成績表。當我走到那塊點著昏黃小燈的白板時,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緊了。所有成績表上的照片,那一個個U都是慘痛的,慘痛的。
一個結了小辮子的女同學,穿著洗得發白的校服,戴著一個髮夾,成績還有兩個C。一切都帶著學生的烙印。只有她那無情的U是超越時間的,以至於考完試的今天,當我看到這張成績單,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如果說她曾把甚麼照片交上自己的學校,那一定就是這一張。(廢話,交上學校的不是用學生照用甚麼照?﹗)
有一個戴鴨舌帽的極可愛的大眼睛男孩,我簡直不忍心正視他的U。他的成績表上,寫有一個小小的備注,備注寫著︰
表現差劣,你的中文口試考官
旁邊還有一個小備注,上面是同樣的字跡
表現太差,你的英文口試考官
他的兩科語文,兩科重要也不可肥的科目。肥了這樣兩科重要的語文科,我很難想像他是在用甚麼來在考試制度中求出路。
U了的是太多了。在小白板上,我不僅看到了一個個努力換來的U,而且清清楚楚聽到了他們在收到成績時憤慨又無奈的叫喊。
在一個女考生的成績表旁,有一張她校內的成績單,成績都有數個A。可憐的考生﹗也許考試時她的確有盡力的寫這許多科的卷,但現在都已不能再查卷。這就是高考強加給人間的悲劇﹗
白板上還有一張特別的成績單,由一A三U四科成績組成。這真是一張特殊的成績,它出自一位高材生的手,它象徵著考生得到一個高分和三個不合格。我無法想象,考生在親手接過這張成績單時,會是怎麼樣的心情。法學院的理想都拋走了,獨獨扔下了荒謬的成績。究竟是制度的荒謬,還是真的沒有盡力考好?
考場外是一片草地,那是畢業生離開學校時,用他們的心去打理而成的。草上有石階,有涼亭,有嬉戲的同學—是那些未經過高考的初中的孩子。石縫間,偶爾伸出了一張張小小的紙條,那是考試前考生、學生的心聲、感情;看著他們的字,我彷彿置身於一片死寂的黑色洋面上,傾聽著極遠極遠的考生留下的種種悲哀的微弱信號。常常地,於寂靜之中,我會突然聽到考生的手又重新翻閱昔日notes的聲音,聽到那些貼在白板上的二十四萬慘然的U,他們的詛咒、叫喊、哀求和拉扯;他們在入U希望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來得及去思、去思、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剝離開了那個學生的時代,成了這社會之中垃圾政府的終生份子。我又想起了白板那些無辜的天真的考生,也許因為他們的存在,致使這社會的每一個良心都在齊聲地譴責。
這就是我的高考
開學前,當我—一個未諳高考的少年,從惡毒的會考中一步跨到了堆滿了U的高考上時,我只是感受了甚麼叫做「壓力」。儘管浸在課程的參考書裏,聽老師說課程急,課程難,讀整整兩年才一個E;儘管看遍了大概數百頁參考資料……我只是感覺到自己像在一夜間長大了,卻還沒有理解高考的底蘊。而這次面對高考,我忽然覺得,自己懂得些甚麼了……
是的,與那二十四萬U相比,與高考目前居然有A的人相比,我的確是來自另一世界的人。我彷彿第一次從考試的角度觀察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的國家。這是殘酷的,也是嶄新的。如此驚人的高考,如此慘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壓力和悲傷,我已經不能用正常的規範來進行思維。那些曲折得令人傷心的題目,那些熟悉得令人腸斷的答案,那些高深得令人發抖的課程,那些強橫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制度,一切屬於人的品質都俱全了。
這就是我的高考。
二零零三年的春節,我是在高考壓力中度過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聽見嘰嘰呱呱的背書聲,過午,那聲音更響,及至薄暮,滿室的背書聲已密得分不出點兒來,整個天空都映出一片通紅﹗我看見桌子上,書堆中,那些高考生正一課接一課地背誦文學和中史︰進學解、三省制、「班超張騫」、「淡黃柳」……聽不見輕鬆的笑聲,只是不停地背、背。我覺得那震耳欲聾的背書聲中,飽含著一種極為複雜的情緒。
高考前訪問過的那位在書堆中咪了十三天的學姊,邀我去她家看notes。在高考中失去了大學希望的孤獨學姊,似乎把我當成了唯一的希望,她一口一個「努力」,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麼沉。原來學姊在裏面塞了一套參考書﹗
我提著沉甸甸的包,在考生的居處上走著。滿地是高考的notes,空氣中飄著咖啡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
除夕的自修室,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考生區燈火輝煌,而那些尚未關門的「小孩區」中,只有暗暗的燈光。但那裏有著真正的人的氣息,不如我這沉甸甸的包裏裝著的學姊的那堆notes。在書店門口,我停住了腳步,我又看到考試前看見過的那一本本西史書。當時,書中是一part高考的課程。西史書書頁仍然不動,彷彿在此起彼落的背書聲中封印起歷史。我的眼睛發睏。考生對這些西史書的理解,也許遠不如它們對人的理解呵。
二十四萬U無疑是一個悲哀的整體,它們在考試後帶走了入U的希望,夢想,使得考生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殘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遺留下來了。彷彿是不再痛苦的痛苦,彷彿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正是這一切,促使我用筆寫出我的高考。我要給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考試學家、心理學家……不,不光是他們,還有人—整個地球上的人們,留下關於一個大劫難的制度的真實記錄,留下關於讀書中的人的真實記錄,留下尚未有定評的制度歷史事實,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問。
這就是我的心願。
備注︰高考是香港中七生要考的一個公開試,一個十分艱苦的公開試
網址:http://boom.u2home.com/big5/article_view.php?Board=322&Art=1881
老奉
距離下一科高考尚有一些時間,近日天氣也實在好得不想溫習,作為新春秋小魔之一,且出來搶佔版面博出位。(順帶一問:西口西面,你究竟算係西魔抑或係魔西?)
眼見反位談中國文化,作為應屆高考生,自然就聯想到 UE (Use of English)。因為中化 UE 兩科,正是高考生進大學的關鍵之一。(嚴格而言,高考生所應考的,只是中化科,而非中國文化,可惜有不少人讀完中化科以後,就以為所學者就是中國文化的全部。)
我得承認自己英文水平奇差,考 UE 也只求一隻 D,故本文並非要討論 UE 這一科,僅是想寫寫近日令高考生分化為兩大陣營的新聞。據網上消息所得,早前 UE section E (Practical skill) task 1 五百字以後並不會計分之傳言,已經作實。
此消息一出,當日並只寫五百字以內的考生自然認為考評局英明,而抱有「最多咪 word limit 度扣兩分,有 point 唔寫就笨」之心態者,亦自然大肆抨擊考評局不公。更有人打算申請法援告考評局。(雖然,只係得啖笑。)反正高考拉 curve,大家一起低分也就罷了。
本人無意斷定抨擊者之動機,但就我所見,有一些人只不過是心有不甘而大呼不公。勢利一點看,能夠寫五百字以內的,要麼就是真正的高手,要麼就是像在下般 只求合格的考生;前者你威脅不了他,後者他威脅不了你,又有甚麼好怕?況且考試本身就充滿著未知之數,就此判定自己有損失,未免過早。
此外,部份人的心理,就像是中了六合彩頭獎後發覺有兩注中,便認為自己「失去」了一半獎金的想法。歸根究底,只是一種「老奉」心態:覺得自己中獎,獎金就「應該」屬於自己;覺得寫了 points,所有中 point 的分都應該屬於自己。
其實不只是 UE 科,就算是其他科出卷爆冷門,總有考生認為考評局犯錯/靠害。(無疑考評局犯過不少錯。)不少人經常覺得卷「應該」是這樣,「不應」是那樣,也只不過是長 久以來大家相信卻未經證實的神話。久而久之,大家就視為「當然如此」的預設。就如 practical skill,自上年開始方有字數限制,但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寫得越多越好,才會有「唔寫埋o的 point 就笨」的想法。可是指引寫明要寫五百字以內,五百字以外的內容並不計分,又有何不合理之處?(且格式、語文的分數不受影響。)
就算退一步而論,我發覺有不少年青人搞不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合理與否是一回事,有權與否是另一回事。我並非要宣揚「權力就是真理」,可就算再不合理,只要你一旦參與這個遊戲,制度下如此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你可以去批評、批判其問題,但別人並非奉旨遵循。就好比在學校內挑戰一些不合理的校規,受罰該是意料之內的事。
"Don't hate the player, hate the game."
祝各位高考生好運。
A Level中化科聆聽考試語音平議
今天休假,在家收聽香港電台轉播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聆聽理解考試。內容大致探討「個人恩義關係」與「法理」,引述了關公義釋曹操、信陵君救趙、「瞽叟殺人,皋陶執法」、武王伐紂、孟子和左傳中有關「徒孫射師公」的故事。我不評論內容,只探討聲帶中的語音問題。
聲帶中老師把「曹操」、「劉備」念成操守的操、準備的備,可是學生們卻念成體操的操、比較的比音。老師堅持正音,學生念俗音是課堂裡的現實,不深責。但老師把「華容道」念成「華山」、「華國鋒」的華我質疑,想在教育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華容道」沒有這一條,我和學生一直都是念如字的。大家是怎麼念的呢?「話」這個音理據何在?請鉤沈。
「皋陶」聲帶中師生皆念「高桃」,可是我從來念「高搖」。查兩岸的辭典皆標Gāo Yáo的讀音,算不算「錯讀」?一些古人的名字是有規定的讀法,比方「金日磾」就要念成「金覓低」(Jīn Mìdī,「金日成」當然念如字)。這些名字除了在學術研究或者文史教學平日幾乎不用,一般人念如字甚至不會念不能怪。可是在考試這麼的嚴肅場合,是不是該從正?
幫人hea做中國歷史功課(其中一part)
歷代對隋文帝與唐玄宗評價的文句
隋文帝
《隋書》志第二十‧刑法:「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
《隋書》帝紀第二‧高祖下:「(高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隋紀四‧高祖文皇帝下:「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禦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逾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烏廷玉《隋唐史話》:「楊堅在政治、經濟、法律、兵制等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做出很大的貢獻。」
范文瀾等《中國通史》:「隋文帝主要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後,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使連續三百年的戰事得以停止,全國安寧,南北民眾獲得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
吳楓《隋唐五代史》:「顯然,隋皇朝中央集權制的加强,對統治全國人民和向外擴張侵略,起了莫大的反動作用,但對打擊地方豪族、防衛外族入侵、以及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還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直接奠定了唐朝中央集權國家發展的基礎。」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賢主也。綜帝生平,惟用刑失之嚴酷;然實勤政愛民,尤有儉德。其於外國,則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貢以自誇功德。既非如漢文、景之苟安詒患,亦非如漢武帝、唐太宗之勞民逞欲。雖無赫赫之功,求其志,實交鄰待敵之正道也。」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總的來說,隋的統一,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隋文帝代周,又結束了魏晉以來匈奴、羯、氐、羌、鮮卑各族統治階級劇烈鬥爭的局面。唯有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結束,社會經濟和文化才有更進一步發展以至開啟盛唐的繁榮統一局面的可能。隋文帝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完成了他所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即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和進一步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時又把王權強化起來,因此,他的業績是值得稱道的。」
傅樂成《中國通史》上:「隋的所以迅速亂亡,與文帝也頗有關係,他雖勵精圖治,但因學識過差,行事有許多不達大體之處。例如開皇初年,遇有水旱凶飢,文帝常以官倉放賬,但他後來日漸吝嗇,開皇十四年(五九四年),關中大旱,人民飢困,當時倉儲充溢,竟不許賑。他對政治,本無多大理想,而又輕視教育,因此當時的政治精神,仍是澈底的功利主義,並無宏遠的建國規模。加以他資性刻薄,猜忌臣下,以致奸佞用事,終於被奸臣劣子所愚弄,變易儲位,覆其宗社。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財富,結果只是供給他的繼承者恣意揮霍;其所揮霍不完的財富,最後也變成隋末若干起兵者擴充實力的資本。」
高明士總校訂:《劍橋中國史》(3)隋唐篇(上)「他是一個相當冷酷,難以親近的人,缺乏吸引人的魅力與親切感,更缺乏容人的雅量。正如蒲貝克(Boodberg) 所看到的,他突然、急遽地獲得權力,使他終其一生陷於極度不安全感而折磨著。……楊堅易於暴怒,有時繼之以痛苦的自責。這點顯然關係到他個人的不安全感,也影響到後來的生活,對於這些事情,我用至高權力的病理學作為依據。他曾經在廷上鞭打某些人,然後又同意他們的陳情,這種情況對天子而言是極不恰當的,因為如此一來,那早先的杖刑是可以免除的。他常常在短時間之後,又再憤怒如昔,以馬鞭打人致死。有時候他對請求皇帝仁慈的諫言似乎聽而不聞,而殘酷的處罰又是經常的事。楊堅是一個堅毅、成功的統治者。他孜孜不倦,勞形案牘,把無以數計的文書尺牘由朝堂攜回寢宮批閱。他似乎經常介入政府的各個階層,有時候猛烈地擠入司法體系的工作中,以其權位審核每一部門的所有重大判決。他獎勵有為的官員,譴責怠職、貪污的官員,早朝時主持、討論國內外政策,追求國家的進步等等。」
唐玄宗
《舊唐書‧本紀九‧玄宗下》:「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貞觀之風,一朝復振。……『康哉』之頌,溢於八紘。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逾三紀,可謂太平。」
《新唐書‧志四十六‧刑法》「玄宗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 。」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二:「唯開元之卋,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又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
岑仲勉《隋唐史》:「開元之治,在歷史上號稱隆盛,舊紀開元十三年,『東都米“豆斗”十錢,青、齊米“豆斗”五錢。』《新書》五一,『海內實富,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論者多歸功于賢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恕,不倖邊功,宦竪不與政,絕外邊貢獻,停道、佛營造,皆切要之圖;璟却諛尚實,不事有奇(崇,開元元年十月-四年閏十二月,璟,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八年正月),竊以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嚴格說來,開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後來崇信方士張果,漸好神仙;並尊奉道教,企慕長生,以是朝野爭言符瑞。他本尚節儉,但後來行為漸奢,益務邊功,民不堪苦。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開元前期名臣輩出,後來乃漸漸接近小人,寵任言利之臣,而奸臣李林甫的執政,尤為政治興衰的關鍵。」
張玉法總校訂《名君評傳》:「自開元中葉以後,玄宗在政治上開始逐漸走下坡路,從胸懷大志,變為渾渾噩噩;從謙虛謹慎、兢兢業業,變為貪圖安逸、驕傲自滿、縱情享樂、不理朝政;從用人得當、任人唯賢變為用人不當、任人唯親;從從諫如流,變為飾非拒諫;從注意安民,變為不恤民苦;從注意節儉,變為窮奢極侈;從精簡機構、裁汰冗官,變為冗官眾多、機構臃腫;從皇帝、外戚不干政,變為干政等。 」
陳致平《中國通史一百講》:「關於開元之治,在中國唐書正史上,當然有許多頌揚的話,這些頌揚的話可能有溢美之處。……唐玄宗做了幾十年的太平天子,認為國家安定強盛,他的生活就不覺的一天天驕泰奢淫起來。譬如在開元之初,他講究生活節約,提倡刻苦,後來到開元二十三年的時候,他覺得國家太平,要表現國家的歡樂盛況,於是大宴五鳳樓,在五鳳樓的殿前,開了一個盛大的同樂會,各種音樂、舞蹈、戲劇,百劇雜陳,讓三百里之內的刺史縣令,都要帶領當地的樂舞伎人,集合到五鳳樓之下來表演,這種歡樂表演,熱鬧喧天,連續了五日之久。唐玄宗個人到了晚年,格外講求享受,漸漸的不問政事;他初年不喜歡和尚尼姑,取締佛教,可是到了晚年,他不僅信佛教,而且好神仙。於是乎他的個人生活,由樸實到奢靡,國家的局面,也由強盛而轉為衰落。這個關鍵,主要在於一個宰相的更變。 」
希望以此祝願四月廿三日考高考中國歷史的考生一切順利。
銀紙,沙紙,廁紙
教育高官涉嫌干預學術自由,全城拍手雀躍,期待大戲開鑼。好了好了,終於開審了,高官真身已呼之欲出,這回你插翼難飛了吧?「說話要小心點啊」,I'll remember this. You'll pay!話口未完善惡因果今朝都到眼前來。如果今時今日還有學校迂腐得要辦道德教育課,這則醜聞真可謂上佳教材。
但回心一想,香港市民也未免太可悲太無助了,因為一個狗官下台,還有千千萬萬個狗官。說他們是狗,我要澄清,我絕非有意侮辱狗,我想說的,是他們不但像狗一般馴服,隨時聽主人差遣,而且他們的「教育使命」,更是要把我們都培育成乖巧敏捷的「狗民」,好使我們一生一世心甘情願地為主人的主人服務。我們既是狗民,他們自然就是狗官了。再強調一次,用狗來跟他們比,我絕不是要侮辱狗。
社會興衰,人生晦明,端繫於教育好壞。但看看我們的孩子,即社會的希望,看看他們究竟正在(忍)受着怎樣的教育吧!由幼稚園始,就要學習各式花拳繡腿的表演,操練連成人也覺得為難的presentation skills,準備好隨時向各界面試官獻媚賣藝。之後一路上少不免明爭暗鬥機關算盡,爭啊爭啊為了爭那一分半grade考高一個名次而平白浪費大好遊戲光陰,努力賣藝獻媚收集獎狀以充實生死攸關的portfolio。對對對,頭可斷,血可流,portfolio不可不夠厚。你是誰,小朋友?對我來說,你的人生沒有意義,因為人生意義不能量度,但不打緊,thank God我們有可量度的portfolio--它有多厚,你的價值就有多高。在現代社會,人生只是一疊紙,最好是銀紙,其次就是沙紙(certificate),都不是嗎?你還可以做廁紙,讓人包包鼻涕抹抹屎。
你想像不到教育現況嗎?那麼請睜眼看看,我們的教育高官到底是怎樣的人吧。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就是香港教育的靈魂人物,她的下場我們拭目以待,暫時不妨回顧一下她的金句:
「常有人說教改難以成功,因為社會一有事就將責任歸咎於教育,如早前有學童遇交通意外身亡,即有人說是因班數不足,有人打劫就會給人說道德教育不足。」--《大公報》,2006年3月5日
「根本上教改咁多學校都做,如果係(教改),點解淨係兩位老師(自殺)呢?如果你認為係教改形成的話。」--《蘋果日報》,2006年1月10日
「好似澳門跑狗咁,前少少有隻電兔,等佢搏命追,只要努力少少就捉得到(以澳門賽狗比喻教師要為學生訂立「看得到」的目標)。」--《星島日報》,2005年12月3日
「辦教育好似食白粉上癮一樣,雖然是辛苦,但當教到精靈的同學,便會忘卻辛勞,九月開學時又再辛苦一番。」--《星島日報》,2004年5月7日
「很多人批評特首,但年輕人最無資格(least qualified)去批評,因為沒有了特首,你們不能得到如此多資源。」--《蘋果日報》,2004年4月11日
「中產失業人士可以考慮去教書。」--《太陽報》,2001年10月15日
「如果有人不喜歡這個遊戲,又或者覺得手中的茶(教改)不是他想要的,便需要離開這個『廚房』。」(以「廚房論」比喻不接受教改的老師,可離開這個行業。)--《星島日報》,2000年11月10日
教育就是神,老早已規劃好我們的一生,最啼笑皆非的是,扮演這個神的,可能就是羅范椒芬這種人。那麼我們有自由嗎?當然有,這是人權嘛。你可以選擇以下其中一款人生:銀紙,沙紙,廁紙。
香港的悲哀
今晨看過免費紙標題,說政府干預團體,使他們不能買到鐘樓的外殼碎片。然後政府更籲抗議人士勿有遐想,不要妄想能買到,因為已經一早送去堆填區云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劉吳惠蘭更答得妙,其言到:「事實好,殘酷o既都好啦,我o既理解就係,嗰個拆咗o既鐘樓,已經送左咗去堆填區,亦都可能已經同啲建築廢料混埋一齊,根本還完唔到o架啦,希望唔好有任何遐想,再去討論可唔可以攞返去重整。」(此段引自am730),似乎政府擺明一副「吹咩」的姿態,拆就拆果然強政勵治,還要漏夜拆,再急急運去堆填區,要你連屍骸也找不到,真未見過政府的效率如此出奇地快。
其實我原本思疑政府這麼趕要拆天星碼頭,背後有一大陰謀也。其實這個陰謀論也不是沒有人提過,不過我卻覺得其可信度頗高。我覺得政府清拆天星碼頭只是其中一樣,它最終的目的是要清洗我們殖民地事代的記憶,今日一個天星,可能他日便是大會堂,皇后像廣場。
試想想,當年鄧小平保證五十年不變,我勸你最好不要信,當然毛澤東也不是說要大鳴大放嗎?最後還不是一個陽謀?回歸後甚麼都變,港督府即時要易名為禮賓府,甚至連學制也要與大陸看齊。雖說三三四與外國普遍的學制接軌,但還不是數學被列為core subject,這不是與大陸的高中一樣嗎?可能有朝一日坐滿賓賓的皇后像廣場,維多利亞皇后換了毛主席,然後一眾賓賓圍著毛像彈吉他,唱唱歌,更可能遲下連皇后大道,彌敦道,羅便臣道,文咸街,英皇道,砵甸乍街,這些全都可能要改作人民南路,解放北路,革命東路之類的街道名。
所以老共講的不要信,特區政府講的更要不信,政府口口聲聲說沒有人反對清拆,連何志平這壽頭也站出來話沒有人反對清拆,然則在鐘樓下那班抗議的人難道不稱作人?又另外網上又有人舉出例證說當年政府口口聲聲說是搬遷而非清拆,現在卻變成了搬遷又清拆,政府的信用由此可見一班。
不過最好笑的便是網上有傳言說政府拆天星碼頭是破了匯豐銀行的金磚不倒風水局,不過這個說笑還可以,千萬不要當真,因為我們只要一看,香港的風水龍脈並非在花園道,而且甚麼下的水勢更非直瀉匯豐。如果真的要這樣說,那末,香港近幾年不停的填海,拉直了海岸線也可以說是破壞了香港的命脈矣。(難怪香港這幾年的運勢這麼差囉)
講起教育改革,今晨搭車看見現代還是英皇教育賣廣告,最後一句口號是考試之必需品。似乎中國人對考試真的近乎著迷,自唐科舉以來都有成千幾年歷史(雖然中國歷史教科書常教科舉始于隋代,但更確切的講法是始于唐),不過我倒有個疑問,如果三三四後,現在香港的補習社會否面臨轉型的壓力呢?雖然將來依然有公開考試,但亦有主要的部份以校內的校本評核(SBA)為主,互相之間作一水平參照(standard reference),所以報習社也許要隨著教改而轉型了。不過補習社只是不斷強迫學生吸收大量資訊,而不給學生思考和分析的機會。 但似乎據布魯納的「發現學習法」(Discovery method)中有六大要素,其中一點很重要,便是要教師以學生為主體,鼓勵學生用個人智慧去思考及分析問題,當然這可能只是老生常談,但這正正是現在考試制度下搞到學生只懂盲目地接受,生吞活剝,不加消化,也造就補習社行業的興旺,難怪連補習天王都話:「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即使一個學生知識豐富,但考試失敗就注定一生失敗。」
雙語教育與真心博士
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所草擬的《報告書諮詢稿》*,近日引起不少討論,有反對者質疑其雙語政策將導致愈來愈多課程由中文轉為英文授課(例如:莊耀洸《中文大學監守自盜?——論校方違反中文大學條例之嫌》),有違中大發揚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使命。
我自己除了認識一些中大畢業的朋友外,基本上和中大沒絲毫關係;而身為香港一個普通市民,當我看到報章副刊大篇幅登載有關其語文政策的討論文章時,我不禁疑惑:這究竟與我何干?而當我讀過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別在語言迷宮裡迷路——語文規劃與語文作育的再議》後,我的疑惑更甚。要闡釋我的疑惑,也為免斷章取義,請容許我先引一整段關教授的話:
語文卓越是一種崇高理想,要達到談何容易。但儘管標準很難訂定,從教育上看,語文卓越的追求總是有軌可循的。我向來有一種觀察,就是一個人只要有一種語文的修養達到了相當的卓越境界,則學起其他語文,只要不太晚起步及摸對門路,亦因能對自己作同樣嚴格的要求而較容易臻於卓越。而更重要的,由於語言運用是人類心智能力的一種高度符號化的活動,故起碼一種語文的卓越掌握,是一個人心智趨於成熟、思想臻於幹練的條件。由於語言現實這無以規避的因素,母語無疑是各程度的學員最易窺見語文卓越堂奧的渠道,就此而言,一個恪守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必勝於一個違背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一個讓絕大多數學員有把握地追求語文卓越的語文政策,也必勝於一個只讓少數精英分子從中得益的語文政策。可惜的是,在回歸後的香港,母語教學雖被提出,但幾許風雨中,其真正意義還未得到明確的定位。這是未來香港政府、各級學術單位、乃至學生和家長都要重新深入反省的。
我想,大家之所以支持中大的母語教育,應不會是由於怯懦或懶散而刻意迴避英語,而是該像關教授所說,力圖「讓絕大多數學員有把握地追求語文卓越」,好使他們有「心智趨於成熟、思想臻於幹練」的條件吧?當然,「語文卓越」只是基本要求而已,中大更有意義的使命,該是「弘揚中國文化、溝通西東」。但問題是,先不論這幾十年間中國文化究竟得到多大的「弘揚」,單就「語文卓越」這個陳義不算太高的理想而言,中大是否僅憑其母語(也不論那是普通話還是粵語)教學便可完成目標呢?如果「語文卓越」確是中大學生的普遍成就,我懇請有高人雅士能具體說明一下,以釋我的疑惑。但如果一直實施母語教育的中大,從來都未能培養學生普遍地具備卓越的語文能力,那請問這個支持中文授課的理由又將從何說起?至於什麼是「語文卓越」呢?我以一介閒人的身份去自訂標準沒什麼意義,倒不如聽聽關教授怎樣說吧:
由於母語是一國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其能否承先啟後,保持活力,全視乎這一群體的成員能否活躍地,甚至創造地使用該語言,和使用到哪一種水平。
我們大概看到,關教授所謂「語文卓越」的定義,至少該包括對那語言有「承先啟後」之功,使它「保持活力」,能「活躍地,甚至創造地使用該語言」。請問中大的學生和教授,有人會同意這是中大學生的普遍語文水平嗎?又有人夠膽說,單憑母語教育,此一水平就指日可待嗎?請大家緊記,我一直都沒審視過「弘揚中國文化」這個至高理想的進程,因為我肯定那是不堪審視的。關教授又說:
當然,母語作育的擔子,大學裡不同科系要承擔的份量大有差別。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些職業性的科系要承擔很大責任,但即使如此,他們仍有貢獻的空間。相比之下,所有理論性學科的責任便重許多了。在眾學科中,我認為人文科學,特別哲學應當仁不讓地為語文作育作最大承擔。
這又令我疑惑:「為語文作育作最大承擔」,為什麼不是中文系而是哲學系呢?如果「語文卓越」真是一種全校都普遍追求的理想,那麼中文系更應是卓越的典範,對不對?而不但系內的學生必為語言高手,系內的教授也當是語文權威,對不對?但如果連中文系教授的中文都不行,那麼這種母語教育還有多大說服力呢?而高呼「要肩負中國文化傳統」的支持者,又是否會感到萬分尷尬進退失據呢?我對中大的教授沒深入認識,只能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他們的印象,如果你認為我說錯了,請不吝指正。

星期天晚上,我又偶然看到《最緊要正字》這電視節目。其實我看過首集後,已對這種硬銷權威、自命正統的手法十分反感,評論見拙作《速寫兩則》、傳惑子《正字陰謀論》及舒爾賽《正音正讀,正音正毒?》。節目每次都邀請一些中大的中文系講師、博士之類來教大家「正字」、「正音」和「正解」,上集也不例外,但當那位鬍鬚博士康寶文出來解釋「狼藉」一詞的源起時,我聽得幾乎噴飯。他說「狼藉」解「亂」,是因為「狼睡在草上,朝早起來時,草被壓得亂七八糟」!我很難相信這種只能在Yahoo!知識出現的「答案」,會由一位本地大學中文系的博士講師,當着全港觀眾面前,以一派自信和權威的口吻宣之於口;更令我詫異的,是這幾天都似乎沒任何人提起這個笑話,相信我現在不提,大家永遠都不會再提,而千千萬萬可憐的觀眾,以後都將會把這笑話奉為圭臬。
「狼藉」意思是「散亂」,但和穿鑿附會的「狼臥草上」全無關係,這根本就是一個同義複詞。《孟子.告子上》所謂「狼疾人」,趙岐注:「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故「狼疾」即「狼藉」,都解為「亂」。《孟子.滕文公上》「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可見「狼藉」又可寫為「狼戾」。說到這裡,大家都可看到「狼藉」根本就不可望文生義地強解。「藉」字很簡單,《說文》云:「藉,一曰艸不編,狼藉」,就是「散亂」之意。什麼是「狼」?這個比較費解,但讀過《廣雅》的人都知道答案。《廣雅.釋詁》云:「狼、戾,很也」;又云:「狼,很,盭也」;王念孫說:「盭與戾同,狼與戾,一聲之轉。」「很」是不順從的樣子,「盭」就是「曲」,故綜合而言,狼(即是戾)有「不順」或「屈曲」之意,與「藉」字相合時,就同是解作散亂不整的樣子。我還可以一直徵引下去,舉各種例子證明「狼藉」不可荒謬地拆開解為「狼臥草上」,但我沒有時間也覺得沒必要這樣做,因為單靠以上提出的證據,相信明智的讀者都會心中有數。
大家都知道,要望文生義是很簡單的,而勤讀多記卻是很艱難的。但如果大家對這些可能花掉你無數資源來建立自己所謂「正統權威」的人都沒有半點要求的話,我覺得那未免麻木得太可怕,也犬儒得太過分了。但願有人在高呼口號,要爭取中文教學和肩負文化傳統時,尚可對自己的激情,抱有一份也許只有對情人才會流露的理性疑惑,輕輕地問自己一聲:喂,你是真心嗎?
注:
*
《報告書諮詢稿》有關授課語言的段落:
7.5.1 英語是國際學術語言,也是很多專業所用的共通語言(參看 4.3.1 段)。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及工程科學等課程,其學科內容的文化差異較少,現代有關的學術論文愈來愈多用英文發表,國際學術會議亦多以英文進行,採用英語學習有普遍、直接、準確的好處,因此,普世性的科目原則上用英語講課。
7.5.2 中文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是開啟中國學術文化世界的鑰匙,中文與中國人的思想精神世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參看 4.3.2 段)。如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科目,原則上用中文講課,並按實際需要適當增加普通話講課的比例;同時亦應開設若干用英語講授的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科目,供母語非中文或有興趣的學生修讀。
7.5.3 粵語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與香港本土生活息息相關(參看 4.3.3 段)。帶本地文化色彩和涉及本地社會政治的科目,以及討論人生哲理的科目,原則上用粵語講課,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