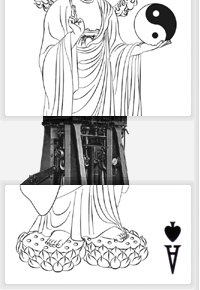標籤:
宋以朗,
倉海君,
魚雁零拾
2008,他逝世已七十年了,終於被安排重現人間。年初,日本出版的《清末小說通訊》有學者談論他;上月中,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在報紙撰文,又說要尋找他。至於我,則是因緣際會地在百年前的舊相片中跟他遇上--他就是鄺富灼先生(1869-1938),民初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英文部主任,亦是ESWN網主宋以朗(以下將簡稱L)的外祖父。
一.偶遇
上星期我在L家看到宋淇先生寫給錢鍾書先生的信(16/1/1985),其中一段令我非常好奇:
上次錢瑗來舍下,文美〔1〕曾給她看一張歷史性照片,乃彼雙親結婚時所攝,時為1908年,可以說是開新式婚禮之先河,居然有bridesmaids。其父為商務首任英文編輯,茅盾曾在他手下做過短時期,其母則為廣州教會辦之醫學院之首屆醫科畢業生。[......]當時錢瑗看後覺得很有意思,內人允代翻印一張,現附上留念。有時給洋鬼子們看看,我們西化已有很悠久的歷史。
錢鍾書覆信(23/1/1985)時則說:「惠寄照相,乃稀世之珍,大開眼界」。既然L家藏此寶,我豈可失之交臂呢?於是連忙出示宋、錢二信,向L索觀照片。可惜他答一時找不到,唯有等。數日後再上去,老工人亞妹--問她張愛玲是誰,她會答「是吃隔夜麵包那個」--已把那張一百年前拍攝的照片放在桌上,還熱心向我介紹相片中人。

照片正面:左起二、三為鄺富灼夫婦

照片背面

錢鍾書覆信
注:
〔1〕文美,即鄺文美女士,宋淇太太。
二.回首余觉立身之道,有三要素焉。其一为努力服务,其次为注重卫生,勤于体操,使身心康健以便于任大事,再次则吾人于执业之余,还有其他活动,以舒身心 之惫乏,而不宜斤斤计较于图利之道也。--鄺富灼,《六十年之回顧》
今天認識鄺先生的人,應該跟知道西籍收藏家
宋春舫先生(L的祖父)的人一樣少,但無容置疑,他們都是中國百年前溝通中西文化的代表人物,與還看今朝的ESWN可謂殊途同歸。要認識鄺先生,我們不妨從梁教授的
尋人啟事開始:
我在此.未圓湖畔﹕尋找鄺富灼
文章日期:2008年2月15日
【明報專訊】我手頭有一個剛開展的研究計劃,就叫「尋找鄺富灼」,英文是Finding Fong Foo Sac,靈感來自一齣辛康納利主演的電影Finding Forester。Fong Foo Sac是誰?他的中文名字是鄺富灼。1869年出生於廣東台山,但十三歲就追隨鄉人到美國謀生。故此有個台山話的英文名字Fong Foo Sac。像許多十九世紀末出國華工一樣,鄺富灼初到美國時,就在三藩市及薩克利緬度的唐人街中找生活。但他的人生歷程和際遇卻與許多早期移民美國的華工(豬仔/苦力)及商人都不同。鄺富灼在美國二十餘年,可以說是一個「衝出唐人街」的奮鬥經過,以及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這是我對鄺氏生平有興趣的第一點。
鄺富灼和孫中山同年出生,同在廣東的僑鄉成長,也同在少年時候離開家鄉出國,不過後來的境遇則各有不同。鄺富灼十三歲離鄉,到了舊金山後,他在兩個華埠(三藩市和薩克利緬度)那裏打工、讀夜校。最後受到一位中國牧師的幫助,信了基督教,並且參加了救世軍,從事宣教活動。這樣的經歷,在當時華人移民中並不常見。
鄺富灼在救世軍中服務多年,並且接受宣教訓練;由於勤奮向學,被擢升為書記,成為三藩市救世軍一名積極分子,更是該會華人分部的創始人。1897年,鄺氏在救世軍工作了八年之後,得到救世軍的資助進入洛杉磯東部的克萊蒙(Claremont)的盤馬奈學院(Pomona College)攻讀大學課程,得到接受美國高等教育的機會。由於我的兩個兒子皆在克萊蒙念大學,故此對鄺富灼的故事也特別留意。鄺富灼在盤馬奈學院讀書的日子並不如意,一方面他要一邊讀書一邊做工來維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卻又因辛勞過度得到了肺結核病,以致需要停學一年休息,幸而最後恢復了健康,並且繼續學業。1902年他從盤馬奈學院轉學到柏克萊加州大學,修讀英國文學,至1905年取得文學士學位畢業。隨後他獲得獎學金再到美國東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主修文學和教育,於1906年取得碩士學位。其後因為有機會和當時中國駐美大使梁誠一席交談,得到梁誠推薦任兩廣方言學堂教習,便結束海外二十四年的漂泊生涯,決定於1907年返國。
鄺富灼回國後,怎樣重新適應中國社會和文化,又如何利用他在美國學來的知識與經驗去為中國謀求改良和變革?這是我對鄺氏後半生的關注所在。鄺富灼在回國後即參加北京1907年舉行的留學生考試,中式第三名進士,授職郵傳部。但鄺氏無意官場,翌年返鄉,迎娶基督徒林憐恩醫生為妻。婚後移居上海,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聘,主理編譯部工作,負責英文書總編輯之職。這是鄺富灼下半生的精力投注的地方。在民國時期,他所編著的英文課本為中國學校普遍應用,而譯出來的外國作品也對五四以後的年輕一代有很大的影響。
鄺氏生平資料並不詳盡,但據我所知,尚有不少親朋戚友,散佈全球。所以我想借此一角,尋找鄺氏親友後人,助我重構鄺氏人生一臂之力。新年伊始,是所願也。
[梁元生 歷史學者、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
但鄺先生在美國的詳細情況是怎樣呢?我們不妨請他現身說法吧。以下我將從其自述之作《六十年之回顧》中節錄一些軼事,希望能夠讓大家看看當年一位知識份子那自強不息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及捨己忘私的情操。
童年他長於農家,生活清貧。據他自述,幼年教育是這樣的:
余八岁入村墊,肄业四年,毕四书,五经亦习一二,顾日后则遗忘殆尽矣。记在塾时,师甚严厉,学生不成诵者,以朱涂面示罚,余罹此刑,不 止一次也。又忆一日,师以事他往,嘱吾辈静坐念书,吾辈待其去后,即喧哗游戏恣意耍乐,不意师忽回,睹吾辈状,大怒,遍挞吾侪,在塾之事,今尚能历历记忆 者,以此为著。
出國他半農半讀,到十二歲便決定到美國工作。臨行時祖母的叮囑,證諸鄺先生以後的經歷,實在意味深長:
余遂于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冬季,偕同行者十六人,离别乡井,向香港出发,临行时,祖母尚健在,祖母倚闾嘱以慎择良友一语,言犹在耳,惟余白美返时,二老已不可复见矣。
香港他途經香港時,有以下經歷:
自余家至香港,今只需二十四小时,当时则需五日之久。海中遇风,船颠簸不已,余等皆大窘,既抵香港,始悉年內无船开行,同人因废然作回家度 岁计,新正始再往港。小住数天,同行中有一童子,年与余相若,同人俱外出,吾与童子,特以年幼奉命留店中,待诸长者去后,吾二人亦潜出游睹,余少见世面, 即本邑县城亦罕至,今骤见香港之繁盛,惊奇不已,终曰走览,不觉倦乏,见两妇衣长裙,雪白之脸,蔽以黑纱,深以为异。又在市中,见摊上售物如糖,购而食之,方悟为西人所用之酵团,寻又见零售劈橘,每片取价一文,余衣袋适有一钱,乃掷诸摊上,取橘一片,置入口中,迨摊主执钱细视,曰,此铅钱耳,余大窘,幸 同行之童,为余代出其值,始得解围,当日之村鲁情形,今日回想,犹不禁哑然失笑也。
抵美華工所受到的美式歡迎:
船抵三藩市(俗称金山大埠),同行长者,示余坐行李货车之顶,往中国市(此为金山埠华人聚店之街)。余初见街上电车往来,心大奇之,时美人之不肖者,见华工联贳入,竞持洋葱 向余辈投掷,此等侮辱,即为余登新大陆,所受之欢迎也。
當時美國政府抵制華工,鄺被迫匿於地室:
当时市政府见华人纷至沓来,而法令又未便施行,为消极之抵制计,乃下令限制每家住户,不得超过一定人数,违者处罚,余因此不敢明居室中,匿于地室数日,其后余转往撤加缅度sacramonts(粵人称之曰二埠以其繁盛及华侨之多仅亚于金山也),投吾叔,吾叔业菜贩,为我介绍,入一美人家当执农之役,每星期得工值金币一元。
鄺曾經在
The Chinese Abroad, 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一書的前言中說過:For was I not spat upon, kicked, stoned, and forced to run for my life time and again just because I was a Chinese?下筆之沉重,足抵一部華工血淚史。
進德修業鄺不久便誤交損友:
余叔虽不学,然知英语可为余进身之益,因命余就中国市纲纪慎(按此为撤加缅度之中国市)教会设立之学校读夜班。余是时年方幼,不经世故,交 友不辨损益,不久遂为恶友所诱惑,习染赌博,并嗜观戏剧,对于学业日渐懈怠,终且辍读矣,而积蓄亦尽罄。此事为余叔所闻,乃向余大加申斥,复命余入夜校肄业。
幸遇良師,扶反正道,亦開始接觸基督教:
时校中之新任教师为陈才,与余初面,即垂青眼,对余百般诱掖,导余于正轨,使余感愧不已。初余不知基督教道,在舟中时,已习闻诽谤教会之言,先入余 心,故余之肄业于该校,纯为英文起见,而对于教会,则抱与我无涉之态度,比与陈君善,受其热诚之感化,余向之成见,始渐消融。同时校中同学之德行,复与余 以良好之印象,余既日与端人相处,久之受其熏陶,颇有向道之意,然胸中犹徘徊万端,不能骤决,则以向日习染,根深蒂固,一时未易排除,且环顾父母亲友,俱 非教徒,苟余一旦进教,彼辈势将与余脱离关系,即余亦常自问,余家敬神拜祖,历代相传如此,苟余皈依基督教,必将与家人背道而驰,诚使基督教之道,能永久 可恃,则亦无他,否则余损失之巨,宁堪设想乎。因是疑虑,顾每与信徒辩论,又终为其道所说服,余之思潮,由是起伏不已,踌躇而莫能决。
自十五至十九歲,他一直寄居教會公所,受益友善士所薰陶;雖然工資微薄,亦不忘寄錢回家鄉:
陈君授余中文与圣道,待余诚恳如家人。西妇加 凌敦Carrington氏,亦刮目相待,授余英文及初等科学,当日所之生理学,天路历程,斐洲游记等书,俱深入余脑中,至今不能忘。每星期加入学道会一 次,按例作学友,如是者半载,即蒙教会为余施洗,而成正式教友,同时余仍执役于人家不辍,所得工资虽不丰,然余能衣食俭约,节省金钱,寄回家中,付还来美 时所贷之旅费,补助家用之不敷,即吾兄之完姻,亦藉余之力焉。
救世軍鄺加入了救世軍,幫忙宣道,但到處受人侮辱,甚至險遭襲擊:
救世军之至西方也,此次原为创见,居民不明其用意,所往视为怪物,无赖之徒,从而揶揄之,百方侮弄,阻其进行,但彼中人漠不为动。其时各派 教会中人,亦因未明其旨趣,讥为无理取闹,自招凌辱,用是彼等所处之地位,其窘苦之状,可想见矣。
该军每聚集时亦嘱余作证,因此而受人之笑骂凌辱,不可胜数,以余为华人,所遭较之西士为尤苦,然余始终不以此为意。
余到各处传道,因余为华人,受人攻击特甚,加以当时太平洋岸一带地方,排斥华工激烈异常,华人无不在危险中。一夕,余独行于路上,突来一壮 夫,向余猛击,余固不敌,又不能逃,正当千钧一发之时,适有一西女士至,见状大抱不平,与之理论,余始得脱难,否则余即不丧命,亦必残废矣。一日余道经一 棒球场,群童见余。即向余追逐,幸余奔入一西女士家中,始告无事。又一日,美国工人大开会议谋抵制华工之策,余方自外归寓,有童子数人睹余,立欲向余包 围,余急走避,彼等亦紧紧迫迫,迨将逼近之际,余见势色不佳,乃掣出身畔小刀示威,彼等始不敢近,然犹遥作恐吓之状,视余抵家门始已。又一次,余至塔哥买 城传道,其时当地之人,已尽逐华人他徙,余之同伴,犹不知余已入险地也,而以为余过此传道一两天,或不致有意外,然余则颇用惴惶不安,是夜余辈方会议间, 突闻门外喧嚷之声不绝,同伴悟为寻衅者之来,乃急着余易装出走,投一友人家,既而友人犹以为未稳妥,复引余跋涉长途至一海湾,在一船上过宿,事后闻人言, 则是夜门外果聚数百人,盖皆欲得余甘心者也。
鄺乘閒進修,成為書記,交往者多有識之士,自此學問大進:
既而余见救世军对于向华侨传道之计划,迄未见实行,颇以留待军中为无聊。乃储蓄意舍去,欲就商业学校,专习“速写 法”及“打字”焉,余以此意陈诸该营长官,并求许余暂离军籍,长官初不允,以为余既有工作,则何用学问为,及见余立志坚决,始可余之请,于是余乃实践余之 志愿,入校数月便毕业。当余求学之时,每曰课余仍如前之工作,赖此以自给。余学艺既成,仍返军中,但不复操烹饪之役,而充书记矣,旋又升为太平洋岸某大佐之书。
余居此任有四五年,在此时期内,余之学业大进,盖每曰所与接触之人,莫不为知识阶级中人,耳所闻者,多为文雅之英语,同时常识亦渐广博,复以当时余有一少年 同事者,为余之金石交,时以进德修业之言相勉励,再则,余于公务之余,暇晷颇多,足资余自修之用,总之,余当时所交之友,及所观察之事物,在在皆可以促进 余知识者也。在此期内,余尝侧身于文艺界,为某文学会员,藉是得探讨古籍,获益良多,余亦尝致力于研究救世军之组织法及管理法。
大學他決心要讀大學,半工讀也不辭勞苦,結果有志者事竟成:
自斯时起,余常觉有更求精造学问之必要,而希冀能入大学肄业,以偿私愿,夫余既有恒业,而犹欲求学者,则以余关怀祖国一念之所动也。余年事 渐长,益觉国事之重要,然念苟碌碌无所长。则曷能为力于国家乎,故余亟欲饱学后方归国,否则宁终老于异域耳。
一八九七年,余以事至加利福尼亚省南部,遇一友人,余告以求学之志,斯友为有心人,后竟为余谋成厥志,余返金山大埠后,友往见盘马奈大学校长,陈述余之愿,及余贫乏之境况,未几该校长适以事至金山大埠,即 来访余,余告以余之多年储蓄,仅得三百金而已,渠谓此数已足为入学之用。余复告以余之半工读计划,渠亦赞成,并促余作速赴校,于是余辞退救世军之职,而入 盘马奈大学为预科生矣。初,余在金山大埠认识之人闻余入大学肄业,均笑余之非计,而欲阻止余之进行,盖当时一般人之心目中,不知有所谓大学教育,况余以有 恒业之人而为此,则更令彼等百思莫解也。
余每日课余,即为人洒扫居室,或打字,或当侍者等役,藉博其微小工值,每届暑期,则往乡间任摘果之劳,凡此种种,皆为金钱起见,至工作之如何卑贱如何劳苦,则非余所欲计较者也。
余因过事劳动,而营养又不足,康健遂互不保。经医生之督促,余乃停学,并在山上一帐幕内逸居,以小休养。期年,余之康健已完全恢复,遂返校 继续求学,四年预科学程,倏忽已满,而升入正科一年级,计余在盘马奈大学肄业凡五年,在此期内,友人时与余以助力,其拳拳意,实余毕生所不能忘者也。余在 盘马奈大学一年级肄毕,即转入加利福尼亚省立大学二年级,三年后,获文学士位,时为一千九百O五年也。
在大学之末年,余服务于校内青年会之 执行委员会,兼充书记之职,自兹起,余之交游渐广,余既毕业于加省大学,同时复得免费学额,乃往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文学及教育学,学年终,余获文学 硕士及教育学硕士二衔。
回國回國後一年,他任教於方言學堂,之後通過考試得文學進士銜,卻棄官不仕,入商務印書館:
一九O七年秋,(光绪卅三年),余晋京应留学生试,获文学进士衔,清廷旋以邮传部某职见委,余接事未几即弃去,盖余私念,时国內方缺乏英文人才,苟余回粵任教席者,以已之资格沦,尚可出人头地,固胜于浮沉无定之宦海也。会商务印书馆颜骏人博士辞职,聘余继其位为英文部主任,正投余之所好,良以余夙主张实事求是,不尚浮华虚誉,文墨生涯,正合余之志。
以上所記,主要關於鄺先生留美時期,回國後的生涯,可參考其自述全文。
三.奇聞網上找尋鄺先生資料時,竟給我意外發現了連宋以朗自己也不知道的「身世大秘密」!國內學人楊揚在去年的《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
《哈佛所見Fong F. See材料》,網上看到的摘要使我大為震驚,原文如下:
摘 要:
在20世纪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期刊中,经常出版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是“Fang F.Sec”。“Fang F.Sec”是谁呢?记得《文汇读书周报》上曾见到过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的文章,谈到“Fang F.See”的中文名字。可是,当时自己是随手翻阅,看过没有再做记录,但在哈佛图书馆的英文期刊中屡屡见有“Fang F.See”这个名字,就开始留意起来。从文章所谈内容,有不少是与商务印书馆和当时中国的印刷出版有关,我猜想这位“Fang F.Sec”大概是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邝富灼(1869~1938)。后来果然在几处英文杂志上见到“Fang F.See”旁标有中文:邝富灼。这证实了我的猜想。而且,英文期刊中,有时不知道是不是排印错误,经常会出版“Fang F.Sec”的文章和介绍他的文章,对照文章内容,我想这“Fang F.Sec”应该就是邝富灼。将“邝富灼”和“Fang F.Sec”输入Google及Baidu搜索,有一些收获。英文的收获,是李欧梵教授在2005年5月15日《亚洲周刊》上刊发的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其中说到自己的母亲就是邝富灼的女儿。[第一段]
那麼李歐梵和宋以朗豈不是表兄弟?!但記得宋淇在信中提及李歐梵時,並沒說過與他有任何親戚關係,如28/4/1982寄給錢鍾書的信有云:「李歐梵最近為芝加哥大學挖去,原隨費正清讀中國現代史,近改修現代文學,人天份極高,文字亦瀟灑,尚有待進一步苦修方可成大器。」僅此而已。
我大感不解,即刻致電宋:「李歐梵是你的表兄嗎?」L說:「你講笑!」然後他告訴我外祖父有四個女兒,最小的是他母親,另外三位沒一個嫁給姓李的......嚴肅的學報論文摘要,難道信口開河?大家都想不通,只好說要找那期的《亞洲周刊》查看。但今天當我再上網翻查鄺先生資料時,終於發現答案。相信誤會的源頭,就是宋自己在2005年寫的文章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Elders,即楊揚所謂「英文的收穫」。文中,宋首先引述2005年5月15日《亞洲周刊》中李歐梵的文章片段,之後再引用外公寫及抗戰時期的書信--楊揚可能英語水平有限,所以便張冠李戴,把宋公子外祖父當成是李歐梵的了。論文摘要居然有此幻海奇情,也可謂中國學術界的奇葩。
3/3/2008補記:1.承上海Vivo兄電郵楊揚的《哈佛所見Fong F. See材料》全文,發現以上摘要內容正是內文的第一段。文末有作者簡介:「杨扬(1963— ) ,男,浙江余杭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議楊揚要引用英文材料時,務必請人審閱一下,以免名譽掃地。
2.掬香齋主人剛電郵給我鄺先生的藏書票:

參考文章:
鄺富灼,
《六十年之回顧》Roland Soong,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Elders張英,
《淺談張元濟和鄺富灼》,收錄於2008.1.1《清末小說通訊》第88期
梁元生,
《求索东西天地间──近代东亚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追寻:以韩国尹致昊、南洋辜鸿铭、中国邝富灼为例》G. Bernard Noble,
The Chinese Abroad, 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 by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V. K.Wellington Koo; Fong F. Sec.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