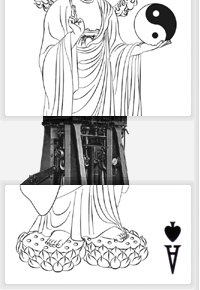今是復活節紅日假期的最後天,明天一早便要上班去也。復活節是什麼節日我想大家應該知道。以前曾經見過一本書寫說,中國人是閃的後裔,又說甲骨文中的帝字即是希伯來之上帝,當然他有他的理據,這在門外漢看來就沒問題,但如果稍加分析,再找找資料看的話就知其胡扯。
於是我今天又來胡扯一番。以我所知聖經中的復活記載,只有新約講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三日後復活這一幕。(當然如果按照ZEKE的講法,耶穌在登山變像的時候已經復活了,是在世復活,我想這有點像佛教之在世修有餘涅槃或道教之言飛升也。)然而原來在早于新約的時代,咱家中國就已經有所謂復活的記載,根據掘出來的出土文獻,差不多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的《天水放馬灘秦簡.墓主記》裏面便記載:「(卅)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大梁人王里□□曰丹□,今七年,丹刺傷人垣雍里中,因自刺殹。棄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雍南門外。三年,丹而復生。丹所以得復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論其舍人□命者,以丹未當死,因告司命史公孫強。因令白狗(?)穴屈出丹,立墓上三日,因與司命史公孫強北出趙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聞犬□雞鳴而人食,其狀類益,少麋、墨,四支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市人以白茅為富,其鬼受(?)于它而富。丹言:祠墓者毋敢嗀。嗀,鬼去敬走。已收腏而□(罄)之,如此□□□□□食□,丹言:祠者必謹騷除,毋以□□(灑)祠所。毋以羹沃腏上,鬼弗食殹。」,又例如《山海經‧大荒西經》裏這樣記載:「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或者你認為這些不是什麼正史資料?那末還有,先看看《漢書‧卷廿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內說:「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這些書成書年份都早於新約又或者約略同時,另外又例如《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九》:「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後漢書‧志第十七‧五行五》:「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後漢書‧志第十九‧五行五》劉昭注補引《博物記》:「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等等等等,若要再舉,例如干寶的《搜神記》,《晉書》、《太平御覽》、《南史》、《新唐書》、《太平廣記》這些書籍都有記者人死而復活的事。
至于扮死的,也有演戲十分逼真,能做到目陷蟲出,如曹植的《辯道論》:「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這真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而就算連佛經內都有不少復活的講法,在此不及細引了。
或許這些可以證明原來中國人的死人復活記載比基督教至少早幾百年。不過我這裏並沒有冒犯基督教的意思,只是提出史實證明,又或者正如以下這幾句經文所說:
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林多前書:15,13-14)
復活節談復活
對話錄(二):芭碧羅與水仙花神話
復活節期間,跟Zeke和.bwd.在Facebook討論Zeke最近修訂的文章《雷電,完美的意念 — 神的伴侶》,大家都想到了一些新東西,現在張貼出來,望大家不吝賜教。先錄Zeke的原文,再附Facebook討論於後。
雷電,完美的意念 — 神的伴侶
《頌詩 — 雷電,完美的意念 The Thunder, Perfect Mind , 在世行者譯》
我是自大能差遣而來,
我來到那些思慕我的人裡,
並展現予那些尋找我的人中。
仰望我吧,思慕我的你,
聆聽者的你,且聽我吧,
一直在守候我的你,
把我據為己有吧。
不要讓我離開你的視野,
也不要讓你所言所聞恨我,
無論何時何地不要昧沒我,時刻謹記!
不要昧沒我。
因著我是首先和末後。
我是被褒顯和被貶黜的一位。
我是娼妓和聖者。
我是妻子和童貞。
我是母親和女兒,
亦是母親的一部份。
我是不育的一位,
卻有著很多孩子。
我是那舉行盛大婚筵的,
然而我沒有任何丈夫。
我是從不曾懷孕的助產士,
亦是自身分娩之痛時的撫慰。
我是新娘和新郎,
亦是我丈夫誕下我的。
我是我父親的母親,
亦是我丈夫的姊妹,
祂亦是我的子裔。
我是為我鋪路者的役僕。
我是我子裔的管治者,
然而祂在我誕辰之先就誕下了我。
在預產期當刻,祂就是我的子裔,
我的能力是源自祂。
我是祂年青時的權杖,
祂是我年老時的拐杖。
一切如祂所願成就在我身上。
《在世行者言》
自埃及《拿戈瑪第古本》的神秘詩歌《雷電,完美的意念》。如此神性第一身斷言式宣告同樣可見於希伯來聖經《箴言》8 章:我 ─ 智慧以靈明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
在造化的起頭,
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
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祂立高天,我在那裡;
祂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
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祂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時,我在祂那裡為工師,
日日為祂所喜愛,常常在祂面前踴躍,
踴躍在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
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不可棄絕。
在這裡作自述的「我」 為陰性的「智慧」 (Chochma) ,根據上文《箴言》指她在神創造萬物之先已存在,是希伯來聖經中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外的另一造物者,以自己為世人母親賜予眾生生命,亦是膏立眾王的「生命樹」《箴 3:18》。被公教稱作「第二正典」的《德訓篇》(原為《本西拉的智慧》)之第二十四篇指「智慧」為「在一切創造之先的首生」,是「純愛、敬畏、智德和聖愛的母親」和「當受讚揚者」;《智慧篇》(原為《所羅門的智慧》)六至十篇則指「智慧」是「造萬物的技師」、「統治所造的萬物」並曾「拯救以色列人列祖」;古猶太以諾傳統中的《以諾一書》則記載「智慧」曾降臨大地遍尋不獲其可住處,繼而返回其原自處;《馬太福音》11:19 和《路加福音》 7:35 亦曾提及此女性神格「智慧 — 蘇菲亞」 (Sophia) :「智慧之眾子都以她為鑒」。從上述記載中可見「智慧」並非僅是擬人法而是實在和獨立女性位格,這就是古猶太的「智慧傳統」。
外的另一造物者,以自己為世人母親賜予眾生生命,亦是膏立眾王的「生命樹」《箴 3:18》。被公教稱作「第二正典」的《德訓篇》(原為《本西拉的智慧》)之第二十四篇指「智慧」為「在一切創造之先的首生」,是「純愛、敬畏、智德和聖愛的母親」和「當受讚揚者」;《智慧篇》(原為《所羅門的智慧》)六至十篇則指「智慧」是「造萬物的技師」、「統治所造的萬物」並曾「拯救以色列人列祖」;古猶太以諾傳統中的《以諾一書》則記載「智慧」曾降臨大地遍尋不獲其可住處,繼而返回其原自處;《馬太福音》11:19 和《路加福音》 7:35 亦曾提及此女性神格「智慧 — 蘇菲亞」 (Sophia) :「智慧之眾子都以她為鑒」。從上述記載中可見「智慧」並非僅是擬人法而是實在和獨立女性位格,這就是古猶太的「智慧傳統」。「智慧」與太初創世之「道」(Logos) 兩者一直有著相當的互換性,第一世紀猶太哲學家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 指「智慧」為一女性神格,同為神的母親、妻子和女兒,他把「智慧」與「道」為陰陽對等的二性 ,兩者共同分享著「神之首生」、「第一序」、「神的代理人」和「人神間的中保」的身份,此詮釋對日後猶太教及基督教有著深遠的影響;《約翰褔音》作者以斐羅對「道」的詮釋為基礎而寫成了序中的「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保羅在《歌林多前書》1:24 提出的基督作為「神的智慧」亦是受斐羅所影響;及後第四世紀亞力山大主教阿他那修 (Athanasius) 在抗衡亞流派時就曾提出「智慧」為神性之首生而說:「子就是父的『智慧』和『道』,且靠著祂並在祂之中創造萬物」;同代的尼西亞神學家維克多林 (Marius Victorinus) 亦相信「智慧」為三位一體的合稱,「智慧」和「道」皆是子的名字並強調「道」為陰陽二性;深受維克多林影響,奧古斯丁 (Augustine) 則指「智慧」為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
在拉比猶太教及猶太秘學均把女性神格的「智慧」視為學習《托拉》(摩西五經)的終極奧義,且稱她為神的伴侶「舍姬娜」 (Shekhinah) ,意為「神的所在處」和「神的榮光」,她曾協助父創世、作為雲彩降臨會幕及 代替父向眾先知顯現。自十九世紀起俄羅斯東正教中就有著一門專研神性女性位格智慧的「蘇菲亞學」 (Sophiology),為俄國現代宗教哲學之父索洛維耶夫 (Vladimir Soloviev) 受十六世紀著名的德國基督教神智學者伯麥 (Jakob Bohme) 啟發而創立。
在《拿戈瑪第古本》中被認為是《約翰褔音》續篇的《約翰秘傳之書》裡,基督在異象中向使徒約翰解說了天上地下一切的由來,當中提到在一切之上有一沒有名字的不可見之靈,祂超乎一般人認知所謂的「神」並凌駕於存在及時空等所有概念,圓滿自在於寂靜的永恆中,在猶太秘學中稱此在四字神名
![Y-H-V-H [泛作耶和華] Y-H-V-H [泛作耶和華]](http://photos1.blogger.com/blogger/485/2782/1600/yhvh2.gif) 之上的不可見之靈為「無量」 (Ein Sof) ,十二世紀自法國普羅旺斯的拉比阿伯拉罕.本.大衛就此曾解說:「基於祂比世上任何事物來得純樸,相比下祂就是『虛無』」。因著不可見之靈是圓滿自在和不假外求的,在祂裡面就不曾存在「我」這個概念,這樣祂便處於永恆的無我止境中。一息間,祂在光映中發現了自己的倒影,從而產生了祂首次的「自覺」,此「自覺」化成了一實在形體,那就是「智慧 — 蘇菲亞」,亦被稱作首意念「芭碧羅」 (Barbelo) ,《約翰秘傳之書》節錄如下:
之上的不可見之靈為「無量」 (Ein Sof) ,十二世紀自法國普羅旺斯的拉比阿伯拉罕.本.大衛就此曾解說:「基於祂比世上任何事物來得純樸,相比下祂就是『虛無』」。因著不可見之靈是圓滿自在和不假外求的,在祂裡面就不曾存在「我」這個概念,這樣祂便處於永恆的無我止境中。一息間,祂在光映中發現了自己的倒影,從而產生了祂首次的「自覺」,此「自覺」化成了一實在形體,那就是「智慧 — 蘇菲亞」,亦被稱作首意念「芭碧羅」 (Barbelo) ,《約翰秘傳之書》節錄如下:祂獨自在圍繞著祂的光中睹看自己,
那是潤澤眾次元的活水之泉。
祂察見自己的倒影落在靈泉的各處,
便迷戀著這發亮之水,
基於祂的倒影就在這清澈的水光中。
祂的自覺成為了一實形,
在光芒中的一個她便應運而生。
她是先存於萬有的首道能力,是萬有的旨意。
她的光反映著父的光,是完美的能力,
是不可見童貞的靈之形像,
她是首道能力,是芭碧羅的榮光,
是眾次元中的完美榮光,是啟示的榮光。
她將榮耀頌讚歸于童貞的靈,因著她本自那靈而出。
她就是首意念,那靈的形像。
她成了萬有的母腹,本著她先存於一切。
她亦是父母一體、首人、聖靈、
三聯之子、三重能力、三名字、
陰陽並存者和在不可見的永恆次元中首現者。
「智慧」就是無我的不可見之靈的「自覺」,此一念將原來靈不可見的形像複製成了實形的宇宙首人「智慧」,為猶太秘學中神性從「無」 (Ein) 到「有」 (Yesh) 之序,亦包含著神屬性中不可知的超越性和無處不在的臨在性的相對關係。不可見之靈是寂靜不動的,祂從不會主動揭示自己及介入世事中,如此地上所有的救贖就是自其意念「智慧」而來,「智慧」不時降臨人間主動地揭示自己,作為反映著不可見的父之光的鏡子 (Ispaklaria) 讓世人能一睹神光,為斐羅強調「智慧」作為「人神間的中保」,這是為何《約翰褔音》 1:8 指「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智慧」作為反映父光的鏡子更能避免人們因直視神光無法承受而喪命的狀況 《出 33:20》(稱之為「神之吻」 (Meitah Be-Neshikah) ,阿伯拉罕、以撒、米利暗、阿倫、摩西皆是死於此情況下)。
一如猶太秘學所說,在太初創世、降臨會幕和聖殿及向眾先知顯現的神性皆不是至高不可見之父而是其代理人女性神格「智慧」,首意念「智慧」就是在西乃山上以雷電展示神性形像者,為之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標題的原意。當摩西問及「神」的名字,所得的回答是「我就是我」(Ehyeh Asher Ehyeh,《和合本》作「我是自有永有」),如此神性第一身斷言式宣告就是「智慧」作為不可知的神之「自覺」向世人說話的特定模式,《猶太法典》 就曾提及摩西領受的「我就是我」之名為見神最清晰的鏡子,在猶太秘學中此名亦是所有希伯來神名中之首,對應首個流溢輪「榮冕輪」 (Keter) ,為與神性相遇最接近的距離。此「智慧」自述風格一直延續至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及《箴言》8 章中且重申著她就是太初的「第一我」,即太初與神同在的「道」《約 1:1》。此外,摩西在西乃山上所遇見的「不滅火燄的荊棘叢」(生命樹)及「雲彩」同樣為古猶太象徵女性神格「智慧」之物,他就在當中被「智慧」膏立從而轉化成一如天使般的神人,這是為何猶太釋經書《米大示》指摩西之銜 "Ish Elohim" 一字該解作「神的丈夫」而非僅是「神的人」。
在古猶太智慧傳統經常以「智慧」一如上文《雷電,完美的意念》中同時作為聖者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在猶太秘學經典《光明之書》(Sefer ha Bahir) 有著此描述:
祂將女兒許配給王者,視之為賞賜。
因著對女兒的愛,
有時候祂稱女兒為「妹妹」,
那是基於他們本是出自同一處的緣故;
有時候稱她為「女兒」,
因為她的確是其女兒;
有時候則稱她為「母親」。
「智慧」本自不可知一源而出,為之祂的女兒;「智慧」內在蘊涵著陰陽並存的神性,為之祂的妹妹;「智慧」在其內誕下了天上人子「細貌」 (Zeir Anpin) ,為之祂的母親。文中的「將女兒許配給王者」就是指神將「智慧」許配給所羅門王《王上 5:12》,成了所羅門王的妻子;所羅門王和「智慧」同自至高者而出,就是所羅門王的妹妹;所羅門王本自「智慧」膏立而得真生命,就是他的母親。
在《拿戈瑪第古本》另一名為《宇宙之源》的經典指「智慧 — 蘇菲亞」自不可見之靈流溢所生後創造天地萬有,她將其自身內在的女兒「祖貽」(Zoe,意為「生命」)許配予天上人子撒寶特 (Sabaoth) ,在創世時將氣息賦予阿當使之成為活人,並差遣祖貽到人間成了眾生之母夏娃以協輔阿當。這樣,她既是天上神性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亦是地上阿當的母親、妻子、妹妹和女兒。在《宇宙之源》中有一段與《雷電,完美的意念》極為相近的蘇菲亞祖貽自述:
我是我母親的一部份,亦是那母親。
我是妻子,亦是童貞。
我是有身孕的,亦是助產士。
我是撫慰分娩之痛的那位。
我是自我丈夫誕下的,
亦是他的母親。
他既是我的父親又是我的主。
他是我的力量,
一切他所欲的,他必帶著理由說出來。
我是成就的進程,我亦已生出作為主的人。
此外,耶穌身邊不同的「瑪利亞」亦可見「智慧」同作母親、妹妹和妻子之說,自《拿戈瑪第古本》之《腓力福音》的段落:
三位常與耶穌為伴的瑪利亞,
就是祂的母親、祂的姊妹、
和那位被稱為祂的伴侶抹大拉。
祂的姊妹、祂的母親和祂的伴侶為三位瑪利亞。
「阿卡莫特」(Echamoth) 和「阿克莫特」 (Echmoth) 為不同的兩回事。
「阿卡莫特」簡而言之就是智慧,
「阿克莫特」則是死亡的智慧,
那認識死亡的一位,
且被稱為「小蘇菲亞」。
耶穌母親瑪利亞乃是「阿卡莫特」(意為「智慧」)一直養育肉身的耶穌,為天上地下沒有任何力量能污損的童貞, 稱作「大蘇菲亞」,如此對照可見於俄羅斯東正教之蘇菲亞學中;而耶穌的伴侶抹大拉瑪利亞則是「阿克莫特」(意為「有如死亡」),她在十架下及空墳之前作為執行耶穌之體被釘死的贖罪祭之女祭司,稱作「小蘇菲亞」。她們皆得著從上而來的智慧,一如摩西姊姊米利暗(Miriam,希伯來文的「瑪利亞」)作為協輔救贖者,籍著她們使道成肉身之計劃得以成就。
按《雷電,完美的意念》所述,「智慧」既是母親、女兒、妹妹、妻子、新娘和新郎,更是童貞 和聖者,這裡的娼妓不是貶稱,其希伯來文 Kedesha 與「神聖」 (Kodash) 為相同字根,而「娼妓」、「聖靈」 (Ruach ha Kodesh) 、「童貞」和「智慧」此四字乃是古代近東對女性神格交替使用的尊稱,這是為何抹大拉瑪利亞同樣被指為「娼妓」。
如此我們就能解讀《多馬福音》105 教人不安的論述:
但凡認識父和母的,他必被稱作娼妓之子。
但凡認識永生之父和智慧之母合一奧義的,就能一如摩西、所羅門和眾聖者般得著女性神格「智慧」膏立而得著真生命。
討論
.bwd.:
I think the status of 圓滿 denotes a 究竟的(修行)境界? I have a little book about Buddha’s life here and it states 佛有三身: 法身, 報身, 化身. 法身 is like The Unknown One: “法界之性, 離一切自性, 無一實體可得, 所以佛的法身雖遍滿虛空法界, 卻無大小之分, 亦無多少、有無、來去、生滅等一切計度分別。” 化身則為世人可見之體, 例釋迦牟尼佛, 世人可觀其修行及經歷生老病死以世事無常之理, "亦能以化身之力從虛空中及樹木草石等懸崖等無心之物, 發出法音演說諸法真實義", which is like Barbelo, a visible side / emanation / part of The Unknown One, who is himself invisible and indeterminate, and Barbelo is the “part” to do the awakening work (because she is the visible side), while The Unknown One remains in Silence and 虛空. Buddha is with the status of 圓滿三身, which can then be best deliver the message to people.
Zeke:
I've asked Tom yesterday and got the term 無明,無始無明 is similar to the Invisible One, while 一念無明 is like The First Thought Barbelo.
Quoted from 《楞嚴經》: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必明即是無明,無明乃為結妄根本。
倉海君:
1.「必明即是無明」?似乎不是這樣,請參考以下網頁:http://www.fosss.org/jcxs/sjcy.htm
Barbelo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细」之「動相」。
2. 「祂察見自己的倒影落在靈泉的各處,
祂便迷戀著這發亮之水」
迷戀二字很有意思。我認為此「迷戀」其實就是創世首日之光:Zohar以此光等同sefirah of Hesed,而古羅馬詩人Lucretius在其《物理論》(De Rerum Natura)卷一也稱愛神Venus為萬物之母。奧維德(Ovidius)的《變形記》(Metamorphoseon Libri)卷三載Narcissus故事,我懷疑原型可能是一段與Barbelo相關的創世神話--這是很離經叛道的解法。一般人只留意到這故事以「自戀」為主題,卻忽略了很多細節,例如Narcissus出生時,失明先知Tiresias已預言「除非他將來不認識自己」(si se non noverit),否則不會長壽。何謂「認識自己」呢?原來Narcissus愛上水中倒影之時(二元分裂,即「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後來當他覺悟到「他就是我」(iste ego sum),卻苦無方法合一,便悲慟至死,形影俱亡。他的影乃由愛慕所生,因為只要他「一轉身,所愛者便會消失」(quod amas, avertere, perdes),然而他卻終日凝視自己,幻象便恆住不滅了。不要忘記Aristotle的神,就是「思想自身的思想」(he noesis noeseos noesis),相信也是Plato甚至更遠古的哲學家遺教,所以我推測Narcissus根本就是由這個至上沉思者發展出來的象徵。另外,Narcissus有一個他不欲接受的「伴侶」,叫Echo:她本來有肉身,後來只剩下聲音。如果美少年倒影是「第一念」,那麼Echo便順理成章扮演《首念之三形》中「聲音」的角色了。
一個有趣的問題:Narcissus未見倒影時,當然沒有「自我認識」,但見到倒影而迷戀它時,又是否有「自我認識」呢?抑或他只是「自我誤解」?我個人認為是「誤解」居多,儘管其「認知」程度可能較最初的「無知」為優。然而自我認知會否陷入困局,即把自我分裂為二呢?天地萬物的創造,又是否源於神的一念無明及祂對自我的誤解呢?(我傾向相信是)
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當然,相對於神是幻象的,對我們這些幻影而言就是真實了。
3. 最近我在讀古羅馬作者的詩文,發現很多有關Sophia的論述,很有趣,稍後有空再撰文分享吧。另外,我對Fideli D'Amore很感興趣,不知大家曾否對此神秘團體略有所聞?
Zeke:
謝謝,當中點出好幾個極具啟發性的關聯。就創世原型問題,對照 NHC 中 Sethian 及 Barbelognostic 幾個流溢創世版本,從不同版本中細節上的差異可見它們不可能出自同一材料或曾互相參考(除了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和 The Hypostasis of the Archons),然而,它們卻像是從不同的口傳而來,這些口傳卻同時指向著相當同一原型。一如你提出的,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Kabbalah 生命樹亦是如此,其對應的五相就是委婉地表達著米索不達美亞的多神神譜和他們古希臘哲學式流溢關係。
NHC 中的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一如你提出把 Venus (Aphrodite) 等同萬物之母:
The second Adam is soul-endowed and appeared on the sixth day, which is called Aphrodite. "
我不認為是這樣的神話角色挪用是大雜燴,我反而認為這樣的挪用表示了當時社會就不同神話間的人物互換有著相當的共識,一如 Magical Papyri 那樣。
Fideli D'Amore 我只知道他們沿用著回教秘學的整套系統和術語,大概是派別的創始人曾受回教秘學的啟蒙,在中世紀初有好幾為西方及猶太哲學家均受當時的回教秘學影響。
.bwd.:
噢, 搬到這邊來哪, 那我在這兒再請教數個問題:
"見到倒影而迷戀它時,又是否有「自我認識」呢? / 我個人認為是「誤解」居多 / 天地萬物的創造,又是否源於神的一念無明及祂對自我的誤解呢?(我傾向相信是)" - 請問你所指的"誤解"是指誤解了甚麼呢?
我覺得天地萬物的創造, 源於至高者的一念, 但在整個創造的舞台上, 也就只那一念, 然後, 祂復又回歸到那深淵。也許是因為祂是完全超脫的, 不可名的, 所以經典上談到祂時也沒有多談祂在創世(指這個世界)的角色只集中談祂的不可名之性。"約翰密傳"開篇便花很多篇幅談到祂的不可見、無以量度, 祂不屬於完美或受祝福或神聖, 因為祂根本超脫這一切。而這些經典用到的字眼, 大多是"存在", 比方說, 在"Allogenes"裡, 對至高者的描述是"He exists as an Invisible One who is incomprehensible to them all. He contains them all within himself, for they all exist because of him. He is perfect, and he is greater than perfect, and he is blessed. He is always One and he exists in them all, being ineffable, unnameable...", 可不可以這樣說, "存在"本身是可以沒有"意識到自己存在"的, 就是說, "存在"本身是一個自在的境界, 是沒有任何主體或客體的認知的。同一經典寫道"it is he who shall come to be when he recognizes himself", 語氣上好像沒有談到祂有"創造"的"意識", 只有"自我"的一念。就是說, 祂的一念, 原不為創世而生, 但祂的一念又確實是流溢的源頭, 因為祂的一念(並非有意識或有目的地)流溢了第一念, 之後有其他的流溢, 而我們世人就是通過第一念(可被認識的)才能認識至高者(不可被認識的)。
"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 - 請問你所指的"自己"是誰? 是至高者嗎? 還是我們凡人? 如果是後者, 我倒相信這光是無時無刻拂照著我, 不過我駑鈍, 還未"看到/感到"。
" 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 - 請問, 遠古的近東是不是文明的源頭? 是不是各種宗教都始於它們? 我在歷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可說是連common sense也沒有, 最近讀一些有關Freemasonry的書, 都由埃及談起, 中間又談到很多神話, 真的讀到頭大。
不過, Freemasonry和Kabbalah的關聯還真有趣。有位叫Guérillot的學者將Scottish Rite中10個Degrees和生命樹各輪做了對照, 出奇地吻合呢。
又, Narcissus見到自己的倒影時, 他意識到那個倒影是他自己呢, 還是認為那是一個他者? 他迷戀著自己的倒影時, 是迷戀著"自己"/"自己的美"呢, 還是迷戀著一個自身以外的"他者"?
自己(一) -- 鏡子 -- 分裂(多於一) -- 意識?/沒有意識? -- ?? -- 合一(一): 這個概念很有趣。
倉海君:
我的想法很簡單:至高者一念成象,頓生依戀(即「光」),由是象復生象,前後相逐,往而不反,既遺忘了自己,亦幻生出宇宙萬物。這過程很簡單,你每分每秒都有此經驗(特別是「遺忘自己」),思想本身就是創造/流溢--不論你有意還是無意。我們一直都在感受着類似創世的過程,只是我們不察覺而已。
我所謂「誤解」,指「不知道那一念而生之象就是自己的思想本身」;正如在水仙花神話中,Narcissus本來也不知道倒影就是自己(有人認為這版本太無稽,便插入孿生姊妹一角,說Narcissus臨泉自照,是懷念已死的姊妹)。換句話說,在創世之初,至高者根本沒有自我意識或知識,而只是一味追逐那作為他者而存在的念頭,且妄執為實,是為「誤解」。至高者的幻想,相對於我們就是現實,所以當祂真正「認識自己」--如Narcissus頓悟倒影之因由--並把其意識流斬斷,萬有就不復存在了。
如Tiresias所預言,Narcissus「認識自己」後便死掉,這裡牽涉一個詮釋問題:死亡是否意味一種解脫呢?Ovid詩中記錄了Narcissus一句話:「死亡於我亦等閒事,因為我可藉死亡而放下煩惱。」(nec mihi mors gravis est posituro morte dolores)不在人世,焉知不是美滿結局?萬有皆寂,宇宙反虛,又有何不妥?說到底,生和死都是同樣令人驚嘆的奇蹟。
最後澄清一點:"創世之光雖然至高無上,但可能照不到自己。" --「自己」即至上神自己。因為祂一直都不能完全認識自己,所以--照我上述的理論來說--世界萬物才可能像現在般存在。
Zeke:
在自戀情意結中的人們往往把「自我」和「他者」混淆在一起,就像追逐鏡子裡面另一塊鏡子的形像,在追逐過程往往讓人忘記最原來的本像,這樣下層的智慧方會作出單方面衍生 Yaldabaoth 如此無知之舉,繼而 Yaldabaoth 自以為「『我』就是神,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神」,宣告「別無他神」那就代表宣告者必須以否定他者才能肯定自己,是缺乏自我認知的表現,不同程度地重覆著不可見之靈自戀衍生首意念的模式。只有不自足者方會無止地追求財富和權力,只有不完全者才會強迫別人相信他是獨一真神。
一個人每天打扮為求愛侶的讚賞,這樣他的愛侶就作為了他的鏡子,讓他從中模造一個能讓別人愛慕的自己,一切源於他的本我對被愛的執著,然而此舉卻無法成就肯定本我的原意,基於靠著打扮而被愛的過程是無止的,是徒勞和無法自在的。
在《約翰秘傳之書》和 Allogenes 中分享著的否定句式段落指出不可見之靈的屬性並不在於祂是什麼,而是祂不是什麼,以彰顯其最原來「無我」的不可知性,稱為 Apophatic Theology 。一如妳提出的,「存在本身是一個自在的境界,是沒有任何主體或客體的認知的」,既是這樣,真正的存在是無須以任何理性及外在因素去證明,亦只有從這些因素中抽離方能達至那自在解脫之境。
就「此原型必關乎到遠古哲學家教導以及再之前的近東神譜結構」,在我現時能定案範圍那是米索不達美亞的神譜結構及神話故事內容對日後的希伯來聖經及猶太教之影響,當然其可涵括範圍應為更廣闊。
Forgiveness (寬恕)
問自己如何才能寬恕回教徒,重獲平靜?
甘地叫他去收養一個回教的孤兒。
在寬恕與善行內,才有救贖。
 寬恕,並不代表你要接受別人的錯誤,而是接受人人都會犯錯的事實,包括自己。
寬恕,並不代表你要接受別人的錯誤,而是接受人人都會犯錯的事實,包括自己。寬恕的目的,不只是為別人拿走悔疚的枷鎖,也是為自己除下仇恨的枷鎖。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zabeth Kübler-Ross) 曾在《用心去活》(Life Lessons) 裏說過:
「我們最需要寬恕的常常是自己。我們必須寬恕自己做過或未能做到某些事,寬恕自己犯了錯或沒有學會某些道理。」
另一位作者,大衛.凱思樂 (David Kessler) 接著寫到:
「寬恕並不是一生只做一次的功課,而是要不斷去做的,那是靈性修養的功課,能讓你心靈平靜,不遠離愛,你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再次打開你的心門。」
 知道《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 會上映,便知道我要盡快看完手上的原著,以免讓電影先入為主。
知道《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 會上映,便知道我要盡快看完手上的原著,以免讓電影先入為主。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 的《追風箏的孩子》,讓心如鉛一樣沉重,墜落到谷底。那份內疚、羞愧、以及將過錯埋藏心底的感覺,是如此真實,叫人透不過氣來。
書中講述的,是在阿富汗的兩個小孩。他們份屬主僕,卻情如兄弟,直到有一次僕人哈桑面對欺凌的時候,身為主人的阿米爾見死不救,懦弱地逃去。由於羞於再次面對哈桑,阿米爾竟陷害哈桑並把他趕走。阿米爾從此陷入無盡的自責之中。
然而,書中卻提出了出路。在阿米爾的長輩拉辛寫給他的信裏,有這麼一段 (p. 290-292;李繼宏譯本):
「你對自己太過苛刻…我希望你會意識到:沒有良心、沒有美德的人不會痛苦…
「你父親的深切自責帶來了善行…這些統統是他自我救贖的方式。當罪行導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獲救。
「如果你可以的話,寬恕你父親。如果你願意的話,寬恕我。但,最重要的是,寬恕你自己。」
最後,阿米爾終於體會到:
「寬恕…並非隨著神靈顯身的玄妙而來,而是痛苦在經過一番收拾之後,終於打點完畢,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p. 348;李繼宏譯本)
或:「那時候的我一直認為是否寬恕,並不是隨著虛浮誇張的神蹟顯現而誕生,卻是隨著痛苦整理,收拾起行囊,在半夜悄悄溜走而萌生。」(p. 356;李靜宜譯本)
 相比起來,提名金像奬的《愛‧誘‧罪》(Atonement),主題是「贖罪」,但在電影裏,悔疚並沒有帶來救贖,而是只是一個虛構的安慰。看畢整套影片,我都沒有一丁點的感動。
相比起來,提名金像奬的《愛‧誘‧罪》(Atonement),主題是「贖罪」,但在電影裏,悔疚並沒有帶來救贖,而是只是一個虛構的安慰。看畢整套影片,我都沒有一丁點的感動。話說回來,我雖酷愛電影,但提名金像奬的五套電影,我當時竟一套都未看過,要之後想辦法補看。看來,不是我實在太忙,便是我的口味已經過時了。
Who Moved My Sushi? An Amazing Way to Deal with Change in Your Life
踏入鼠年,大陸先有農心蝦條內藏鼠骸,香港復有鼠崽現於壽司店明目張膽覓食,民眾莫不驚駭.
據報,即日起, 該店將有以下舉措:
1)順理成章,推出優惠,如顧客能正確估中全店老鼠數目,將可全年免費任食魚生拼盤.
2)於輸送帶上設置捕獸器,迴轉不停,嚴格監督,全面確保食客安全.
3)貼出告示,呼籲顧客一旦發現鼠踪, 必須以塑料蓋子即時堵截,及通知職員撿走,否則貴客自理.
睽違十七年!經典再現!《圍城》被拍成法國獨立短片!
 圖:他不是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而是陳道明於九十年代飾演的方鴻漸。
圖:他不是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而是陳道明於九十年代飾演的方鴻漸。改編自錢鍾書先生之長篇小說《圍城》。僅二十一歲、現居法國的業餘導演尼可拉斯〔暫譯〕成功將整部原著濃縮至三十八秒。全片並無對白,卻精煉表達出錢氏於小說內刻劃之「圍城」心態,更忠實呈現書中廣為人知的法國諺語:
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 : ceux qui sont à l'extérieur souhaitent y rentrer, et ceux qui sont à l'intérieur souhaitent en sortir.
「婚姻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最後那隻昏頭昏腦的、應該就是法國版的方鴻漸。
另附:導演加長版〔英文字幕〕
Abnormal (變態)
精神病,或所稱黐線、神經病、思覺失調等,屬於「變態心理學」(Abnormal Psychology)、「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y) 的範疇。
要知道,「變態心理學」裏「變態」的英文是「Abnormal」,技術上即遠離了「常態曲線」(Normal Curve) 中心的平均值 (Mean);用正常人的說法,即和大部分人不一樣。因此,好像「同性戀」便曾出現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第二版裏 (DSM-II)。「同性戀」不是病,但亦不是社會主流的性傾向,所以是「Abnormal」。當然在第四版 (DSM-IV) 裏已被剔除。
既然每個人基本是都有其獨特性,那每個人都不是「正常」(Normal),每個人都有「病」。
在心理學的研究裏,一般會將「正常」定在 95% (Alpha Level = 5%)。於是,智商 (IQ) 高於 120 的便成為天才,低於 80 的便是弱智。如果將「正常」定在 99%,那所謂正常的智力便會在 74 到 126 之間。 這種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做法,忽略了人的智慧有很多種;無論你的智力測驗有多少題目,都不能計出一個分數作為總結。於是心理學家便由「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或譯成「定量研究」) 逐漸轉向「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或「定性研究」)。
這種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做法,忽略了人的智慧有很多種;無論你的智力測驗有多少題目,都不能計出一個分數作為總結。於是心理學家便由「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或譯成「定量研究」) 逐漸轉向「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或「定性研究」)。
「質化研究」不再關心搜羅幾百人做統計分析,而是針對數個或十多個個案,進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內容包括訪談、觀察、日誌分析等。例如,港大社會科學院對特首施政滿意度的調查報告,屬於「量化研究」;港台節目《鏗鏘集》則是「質化研究」。
現今的研究方法,從實用主義 (Pragmatism) 那「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精神上,發展出第三波的「混合研究」(Mixed Methods)。既然一邊要有量化的智商值,一邊又要包含多種智商,那唯有先用「質化研究」羅列出智商的類別,再用「量化研究」來定出 IQ、EQ、LQ、AQ 等等琳瑯滿目的量度標準。
個人認為,大部分人都有病:把快樂留在過去的人,便是「抑鬱症」;把快樂寄託在將來的人,以至總是患得患失、充滿恐懼,便是「焦慮症」。乾脆逃避快樂、背棄社會、抽離自己、熱衷宗教、或以為自己能成仙成佛,便是「精神分裂」。順帶一提,很多人誤以為「精神分裂」即「多重性格」,其實兩者完全不同:前者常產生妄想或感到受迫害,後者則是部分記憶被壓抑以至分裂的後果。九龍皇帝曾灶財便算是患有「精神分裂」。
所以很多人提倡「活在當下」。快樂,當在當下尋;只是也不能不顧及將來。
 最近,哈佛一位很受歡迎的講師 Tal Ben-Shahar 出版了一本書,叫「更快樂」(Happier: Learn the Secrets to Daily Joy and Lasting Fulfillment),紀錄了他那「正面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課程裏的精華。他提到,大部分人不是懷緬過去的快樂,便是在汲汲追求將來的快樂;也有人以「活在當下」之名過著「享樂主義」(Hedonism) 的生活。
最近,哈佛一位很受歡迎的講師 Tal Ben-Shahar 出版了一本書,叫「更快樂」(Happier: Learn the Secrets to Daily Joy and Lasting Fulfillment),紀錄了他那「正面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課程裏的精華。他提到,大部分人不是懷緬過去的快樂,便是在汲汲追求將來的快樂;也有人以「活在當下」之名過著「享樂主義」(Hedonism) 的生活。真正的「更快樂」,他卻認為,來自能持續的快樂:即能由現在延續到將來的快樂。例如,今天不上班,是享樂主義者的「快樂」,但不能持續;找一份快樂又有意義的工作,一方面讓你今天上班上得快樂,一方面讓自己將來回想時亦覺得快樂,才是持續的快樂。這裏一方面針對享樂主義者對短暫快樂的追求,另一方面更是提醒那些想著「四十歲前賺夠二千萬去退休」的朋友,別要為了將來的安逸,犧牲現在的健康、家人等等。其中一個他叫大家想的,是什麼是一份工作 (Job),什麼是你的事業 (Career),又什麼是你生命裏的召喚 (Call)。
祝各位「變態」的朋友,生活得「更快樂」。
市儈父大戰忤逆仔
作者:左冷禪
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上星期初法庭上映了兩齣內容截然不同的好戲,這邊廂有孝子陳奕迅傾家蕩產請御用大狀幫貪污瀆職0既父親上訴減刑,雖然無功而還,但陳奕迅前後為佢老豆單案聘用咗兩名silks(郭棟明同Andrew Macrae),果兩筆數絕對唔係小嘢,其孝心幾乎令我感動得流下兩行男兒淚;那邊廂就上映另一部不孝子被老豆老母追數既黑色喜劇:
博士子減家用 父母索回留英學費
2008年3月4日
【明報專訊】年輕時由衣車學徒出身的老翁,與妻子含辛茹苦為4名子女供書教學,其中本來學業成績不佳的次子,在父母的經濟支持下往英國攻讀學士及博士課程,獲得佳績。惟當眾子女事業有成之際,次子與父母關係轉壞,雙方只靠社工或律師溝通,及後甚至為錢債對簿公堂,父母向次子討回88萬元供書教學費用。
原訴人夫婦為陳炳昆及郭少清(均為譯音),被告是37歲的次子陳文煒。案件經審訊後,區院昨頒下判辭裁定原訴夫婦勝訴,次子須向他們清還88萬元欠款。
判辭指出,次子於中五會考時成績欠佳,1993年父母應其要求,出資支持他往英國攻讀機電工程學士;兩年後,他在父母的經濟支持下再攻讀博士課程。至1998年,次子學有所成回港工作,並與父母及胞弟同住,每月給8000元予父母作為家用。
父母買樓 子每月交租償還
2000年底他打算買樓結婚,與父母商量後,決定與母親聯名買入青衣翠怡花園單位作為新婚居所,百多萬元的樓款及其他雜費由父母支付,次子每月則向他們支付7500元租金。
2003年,次子誕下女兒,女兒與印傭在父母家中居住,而次子及妻子亦會在父母家中吃飯,當時次子每月共向父母支付1.4萬元。
子減家用關係即轉差
但至2005年6月,次子希望女兒及印傭返回青衣居住,他與妻子亦不會再在父母家中吃晚飯,次子便將「家用」減少一半,每月只給父母7000元,自此親子關係轉差。
父母:其他子女有還錢
父母一方指出,當年只承諾借錢予次子出國讀書,2005年10月與次子關係惡劣,次子曾承諾還錢。另外,曾向原訴人借錢讀書及考車牌的被告胞妹及胞弟,事後亦有向父母還錢。
不過,次子否認借貸,亦否認曾承諾還錢,更指父母道德上有責任為他供書教學。
法官認為原訴夫婦對4名子同樣愛錫,被告本身有穩定工作及收入;而被告在2005年10月將青衣單位業權轉予父親,當時雙方關係已轉壞,但次子每月仍向原訴夫婦付款,故法官認為該些款項其實是被告的還款。
睇新聞大大標題話老豆成功向個不孝仔追回留學學費,真係差D以為個Deputy Judge係忽上腦,因為法庭淨係講法律,縱使百行係孝為先,但呢D人倫家事又關法庭屁事咩。單單不孝絕對唔係cause of action,報道又無話父子雙方有任何協議果筆留學費係當作借貸,咁即係又無contract又無meeting of minds/consensus ad idem,咁個忤逆仔又點會輸呀?殊不知睇番個判詞,方知咸豐年前個衰仔同老豆已經有共識筆錢係借既,要還,而更令人詫異既係佢哋冚家都有個怪習,興D仔女讀書留學用既錢係好似滙豐恒生咁當借番嚟,連個細仔學車D學費都係要還番比父母,我不期然心諗,咁佢哋老豆同老婆行完房之後,又會唔會比番一千幾百個老婆呢?
其實呢單案個爭議性都幾大。首先,父母給予仔女既嘢或者長輩俾後輩既野,法律都會以presumption of advancement/gift原則當作禮物處理,當然呢個假定係可以被推翻(rebuttable),响Lily Cheung v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1987]3 HK(30)中,法庭話基於女性社會地位同賺錢能力既提升,令原本丈夫俾老婆當係禮物的假設推翻,但個衰仔當年無錢,個老豆支助佢留學係天經地義,老實講生得佢出就預咗要養,吓吓諗住要個仔女大左之後點樣回報就聽打靶啦,做人咁計咁就不如一個都唔好生,因為子女多數都係liabilities多過係assets,不如慳番D錢去賭狗賭馬或者賭吓金絲貓仲實際。
不過就算當年個死仔有應承還,但從合約法既角度,呢個口頭承諾未必enforceable。因為合約要有效,一定要有四大元素﹕offer + acceptance + consideration + intention to make legal relation。讀過法律都知domestic arrangement係被法庭定性為無法律關係意圖。Balfour v Balfour [1919] 2 KB 571話老公老婆既協議係無法律效力﹕
Nobody would suggest in 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at those agreements result in what we know as a contract and one of the most usual forms of agreement which does not constitute a contract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rrangements which are mad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to my mind those agreements, or many of them, do not result in contracts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what as between other parties would constitute consideration for the agreement.
另外有單叫Jones v Padavatton[1969]WLR 328,個老母大隻講叫個女炒美國老板魷魚返英國讀法律,話事後每個月俾二百磅佢,點知賣魚佬洗身無哂聲氣,法庭都話呢樣係無得告。不過凡事梗有例外,如果响大家關係唔係咁妥既時候立既約法庭就會當堅嗱(Merritt v Merritt [1970] 1WCR 1211)。但係香港果個衰仔同老豆借錢果陣關係明顯和睦,否則個老子都唔會騷佢,所以我個人認為兩人之間借錢還錢約定根本就唔係合約,但奇怪既係個狀又無拗呢點,個官响判詞第33段提過"As a matter of law, the alleged loan agreement would be void for uncertainty or there was no intention to create any legal relationship"後,呢個 point就潛咗水,不過如果個狀無plead呢樣嘢,法官係唔討論既。
個衰仔請個位狀叫Tony Li,好junior,06年call bar。但佢都識個「合約」既無提還款限期,又無話點樣還,咁環境就由個度縮老豆最後磅水果日起計,六年內就要追,否則就過期。換句話個老豆响1998年3月31日最後過水俾個死仔,咁個老子入稟追討既限期就响2004年4月1日完咗。本來就已經係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殊不知個衰仔响2005年12月30日同老豆老母協議還番D學費,咁就仆街啦,因為咁樣就令原本既追討時限復活,個官响判詞73段都話﹕
I think the more probable inference is that those sums from 30 December 2005 onwards were nothing but repayments of the loans. In the premises, the Plaintiff's cause of action was reactivated from 30 December 2005.
再者你走去還錢,即係用行動推翻左之前講果D咩presumption of advancement/gift。反之如果個仔一毫子都唔還,咁個老豆老母就輸Q硬,所以個仔唔係衰忤逆,而係一衰心胸唔夠狠,俾人哦多兩哦就還水,二衰還錢前唔揾個律師問問,好多香港人就係咁抵死,諗住慳果一個幾毫,點知往往就因為咁捉哂蟲,死咗都唔知咩事。小弟意見永遠係事前既準備部署永遠比事後補救來得實際,不過問嘢請唔該俾錢,無錢鬼得閒啋你。
不過我相信點樣既父母就有點樣既仔女,為人父母物都要做仔女既回報還錢,你咁市儈現實,不如索性做愛次次帶套兼體外射精,一個都唔好生,生得佢出,除非佢讀唔成書,否則供書教學筆錢就唔慳得,攬住咁撚多錢托咩,死咗咪又係要今夕吾軀歸故土,所以阿陳炳昆同阿郭少清,你哋咁告個仔,其他果幾件依家仲可能對你無乜嘢,不過遲吓肯定係久病床頭無孝子,死後靈堂冷清清,你兩支老柴到時就唔好長嗟短嘆,怨天尤人。
觀«弄臣»小記 – 亦始, 亦終
於高座聆聽Duke (Valter Borin), 似隔重輕紗, 本懷疑 "廁身" 高座 (廁身者, 亦五百餘港元), 音色定必較差, 然比較Rigoletto (Lucio Gallo)演唱, 似乎乃Borin未盡情發揮; 後於第三幕易角, 想Borin是夜大概抱恙上陣。第三幕換上Francesco Demuro, 此君聲音清脆亮麗, 然就演繹Duke而言, 則金石有餘, 優柔寡斷不足, 吾寧選Borin。然余實不應苛求之, 吾耳早被畢約齡天籟之音(縱余素厭Duke之輕薄不專及撒謊劣行)寵壞, 圖比較二君, 未免過份。
Elena Mosuc演唱偶或迷失(尤其 "Gualtier Maldè; Caro nome")。觀整體演出, 非不能也, 乃缺乏信心也。此乃歌劇大忌, 因歌劇多非自然之音, 需非常信心以演繹。此外, 現場演出有別錄音, 在於現場演出不獨講求歌唱技巧, 亦需顧及情感表達。"Mio padre! – Dio! Mia Gilda!" 一段余愛之期待之, 然起句 "Mio padre!" 顯然未曾投入。Gilda與Duke之愛情, 與Rigoletto之親情, 似乎熱身不足, 可待更進一步。重點仍在 "自信" 二字。
然瑕不掩瑜, Gilda與Duke對唱("Giovanna, ho dei romorsi"), 餘音纏綿, 實動人心弦。及至第三幕 "Un dì, se ben rammentomi", 四人對唱, 和聲平衡悅耳之極。
Lucio Gallo於 "Cortigiani, vil razza dannata" 一曲, 愛女情切, 余認為屬上佳演出。
高空俯瞰, 場景小巧精緻, 雖不同La Scala之深廣, 亦別有一番風景。堂座觀眾許更能欣賞此confined setting之聲效。余處高座, 始終懷疑人聲未能全達乃為此confined setting所困, 然未能證實之。
余不取觀眾於每曲完結時鼓掌之行徑。返家翻數歌劇現場錄音一聽, 未聞每逢曲終皆需鼓掌; 余只知幕終或劇終, 燈亮謝幕方應鼓掌。此非流行音樂演唱會, 觀眾喜歡演出, 可待幕終或劇終致意。更可厭者, 一曲未終, 已急不及待鼓掌並喊 "Bravo!"。賣弄之心昭然若揭, 卻未細想此舉打斷整劇脈絡, 對樂團亦欠尊重。歌劇非只人聲, 音樂亦為一十分十分重要之元素, 當嚴肅欣賞。
亦甚難明, 理應投入於樂曲之際, 何解左右竟陸續傳來手袋拉鏈聲 / 膠袋聲 / 喝水聲 / 搔癢聲 / 竊竊私語聲, 真箇氣不打一處來。ZIP, ZAP, 竊竊; ZIP, ZAP, 竊竊; ZIP, ZAP, 竊竊, 此起彼落, 像煞黑膠唱片之 "炒豆聲", 哈哈, 不禁嘆句: Ahi! La donne! 可話說回來, 歌劇, "鬼佬大戲"也, 古時劇院, 有如大戲戲棚, 乃一消遣閒聚之所, 飲食有之, 傾談有之。念及此, 余自忖, 香港觀眾乃具古風, 哈哈。
若非小克萊伯自沉淵歸來, 重執指揮捧, 余今後當謝絕於香港之古典音樂演出。及後每當起購票之念, 當重閱此文而加三思。或若他日餘銀足而能包廂欣賞, 則無此顧慮矣。
梁祝
去年七月,臺灣新竹市一名國一生透過線上遊戲邂逅就讀高中二年級的男生,初次見面時即遭遇對方強吻。其後二人相約在該市的縣立文化中心見面。國一生憶述被對方擁抱、和進行舌吻。十月,國一生被高中生帶往偏僻的竹林,開始發生親密行為。兩個月後,國一生獲邀至對方家中作客,於書房內展開性遊戲。對方模仿成人錄像情節,將其生殖器分泌的鹼性膠狀液射往國一生面部〔俗稱「顏射」〕。二人以「寶貝」相稱。當時對方的母親在家,毫不知情。
及後,國一生向同班女生透露戀情。女生即時利用網路向另一方查證,經證實後通知校方。校方知會家長。國一生的家長本只要求雙方斷絕往來,但或因後續賠償事宜無法談攏,最終交由警方插手。
高中生被指控性侵犯,他對警方說,二人皆出於自願。警方訊後依妨害性自主罪嫌,將他函送法辦。事件成為臺灣傳媒的一則小報導。
報導指,國一生姓鍾,男性。
香港戲場工作者林奕華以教學為由,向接受創意培訓課程的教師們展示私藏的錄像,片段中的男生不斷互相口交、手淫,並無其他情節。它被專注內容和拍攝技巧的女學員陳曉蕾指為沉悶。林奕華即時訓斥女學員,堅持那是叫不敢面對,同時形容對方永遠不會成為好老師。女學員推論他接受不了同性戀不再是禁忌。林奕華轉而向學員的高層申訴。事件擾攘多時,土耳其軍隊已於二月二十九日撤出伊拉克北部,美軍至今依然不肯撤離伊拉克。女學員表示無奈。
據悉有香港市民為安慰林奕華,已將上述的港外小報導轉寄到其電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