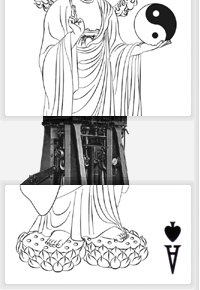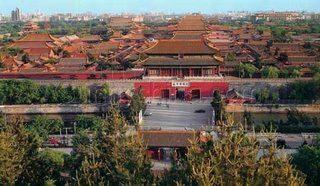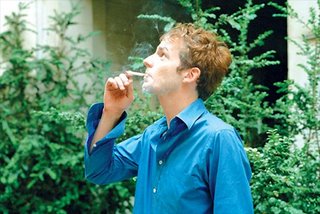標籤:
倉海君,
戲如人生
昨晚見到「法國妹」的msn個人訊息說:
「訂票開催」--乜X野中文?oh,現在的電影節真無文化!
好奇一問:「咁X正嘅中文邊度有?」
原來是
電影節預告片的最後一幕。什麼是「訂票開催」呢?即使起乾嘉諸老於九原,再窮盡他們的所有音韻訓詁知識,恐怕也無法解得通。「開催」大概是日語吧?但為什麼要用日語呢?是因為「開催」本身有中文所不能表達的含意嗎?我只好承認,我跟時代太脫節了。
之後我又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msn(此人非常神秘低調,所以我打滿格仔),聊起電影節會看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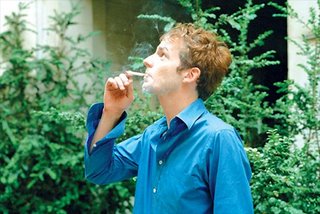
(《毒校草》劇照)
Magliabecchi 說:
有冇邊d你會認為好好睇?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um.... 我暫時仲揀左呢d
超完美地獄
獵男閉路
毒校草
立嗆師列傳
奪面煞星寶萊塢
愈扮愈開心
暮色燈火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說:
仲有Visconti的
LudwigMagliabecchi 說:
四粒鐘,一失足成千古恨。暮色燈火、毒校草我都會考慮,但我見d時間地點好唔方便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毒校草我好想睇
但時間同地點真係好唔方便
我為左睇佢一套,要請一日假~~~
四粒鐘我都係考慮緊
Magliabecchi 說:
要請假睇毒校草?咁我都要睇下啦,我其實都識唔少毒校草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咦?我想睇o個套係四分鐘,唔係四粒鐘~~~
Magliabecchi 說:
四分鐘?你買飛睇trailer?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我係純粹因為"導演乃著名思想家皮埃.布迪歐之子,原是哲學教授改行執導"呢句而想睇毒校草~
你識d咩毒校草呢?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唔係呀,我係話個戲名係"
四分鐘", 唔係"四粒鐘"
Magliabecchi 說:
毒校草=損友(好似我呢d咁) ;四粒鐘係指Ludwig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說:
um....... 好難想像校草一詞同你可以扯上咩關係~
hkiff今年有套戲叫"四分鐘"啦~
Magliabecchi 說:
shit, 法文係les amitiés maléfiques,即「損友」,「有害的友誼」,關校草咩事先?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我唔識法文,但見佢個英文譯名係"poison friends" , 都知個中文名係亂黎
不過唔緊要,反正關唔關校草事唔係我買飛o既考慮
Magliabecchi 說:
睇番上面段「四粒鐘」對話,真係好鬼無厘頭,你都唔知係咪玩野,不過都幾好笑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說:
只係一場誤會o者.....
不過唔知點解,我成日都會發生呢d誤會.... 所以成日都笑埋d無聊野~~~